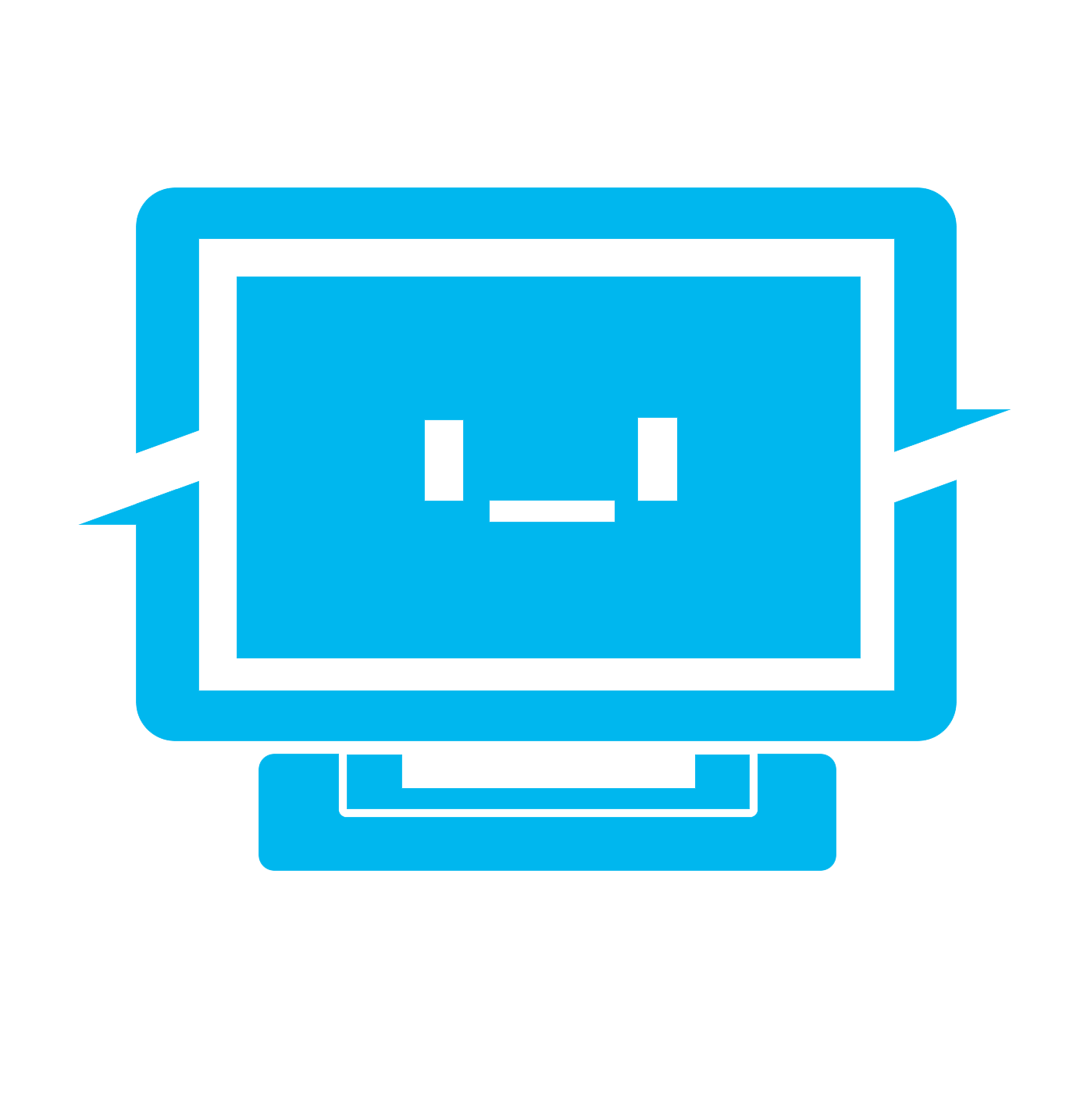非常羡慕@研冰的有一点,她的公众号可以随地插入音乐!(虽然也只能插QQ音乐也很难受)。阅读本篇周报时建议去听以下三首animenzzz的钢琴:
罪恶王冠-Bio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P4y1G7ze
罪恶王冠-Departure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s411h7b8
哈尔的移动城堡-人生的旋转木马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b4y1t7Xj
@酸菜鱼对我和@研冰的关系的评价是“充满了奇诡爆裂但同时又能走得非常平稳的一段”。
抛开这个预测不谈,自私地就我个人而言,这个暑假到现在为止,我在各种感官上实在是——奇诡爆裂。直接的表现是,好像身边的很多人一下子都脱了单,而那么多事情,如此多的旅行、感情、实习、研究、交流……被压缩到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翻翻看一两个月之前的周报,那个时候我刚刚买下显卡,做好了呆在寝室里敲两个月代码的准备。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不要让自己的大学后悔,至少在暑假的两个月要让我的电脑一直运作。但我怀疑一些事情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就像是,在《命运石之门》里的某个时刻按下了D-mail的发送按钮,关于我的整个世界线发生了变动和偏移。
6月21号的时候我对@酸菜鱼说,我处于一种,“积极期待”自己感情发生的状态。脱单这一件事情,看起来只是感情,但实际上是一个人整体的状态的一种表现。我不准确地说说,可能具体体现为,一个人是否还有精力去执着,有耐心去包容,有信念去喜欢和爱。
事实上在六月底我明白必须要抓紧好好燃烧自己的时候,我对很多很多未来的事情(不仅是感情上)都预留了精力和挫折的底线,但是事情发生的比想象的要来的顺畅很多很多,并且迅速很多很多。似乎在我正准备主动去拼一把的时候,有太多的幸运就降落在我身边。6.1号当我按下抢购键的时候我不知道整个七月电脑配件价格一路上升,并又重新陷入缺货状态,intel财报亏损,三星等内存厂商减产,英伟达延迟发布40系显卡……现在在等显卡的人仍然在大骂奸商和矿老板,他们在评论区张牙舞爪的样子和两个月前,两年前没有变化。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还在那一群叫着矿卡的人群里。
也经历过一些被愤世嫉俗和唾骂现实的思绪裹挟着的时间,那是人在大学生活里找不到真正支点的时候。我听到那些人的道理,他们一个说的比一个有理,但是我听累了,我需要专注做些自己的事情。我和我妈说,我从初中以来就很少交到班级或者学生组织以外的朋友,然后我们一家人终于惊奇地发现,这几年来,我们常说:“和这个很厉害的学长加个微信吧”“和以前的某某同学要保持联系啊”,而没有说“噢,他一样喜欢什么,可以互相要个联系方式吧”。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想要加入到画社里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每次我妈给我推微信的时候我会有点本能的抗拒,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两位准大学生学弟加上我微信之后我几乎以呵斥地态度告诉他们不要浪费毕业季暑假的一分一秒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也不要和我谈有关学习的半个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问过那些学长学姐们,他们在谈恋爱吗?在玩什么游戏?暑假回家吗?还是会去旅行?我觉得我以前没有真诚提出这些问题的心境,而一切都显得刻意。
寡得太久了,就会把自己逐渐放入到情感市场的世俗体系下面,自愿地被他人凝视,就像离群太久了也会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与处境为何。我从来没想过和@研冰会这样开始,在外人眼里我们前期或许真的进展太快了,但于我们而言或许是从未有过一个这样的人可以如此信任并接住对方的过去。我从来没有觉得信任和喜欢可以这么快发生,但事实如此。这些事情就是在我犹豫是否要做出一些改变来迎合凝视的时候发生的,会有这样一个人告诉我有很多事情并非没有价值,很多特质会有人喜欢。
我发现我似乎从来都持着这样一份心态,总是想去追寻一些恒久的凝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失去了许多敏锐的感知,变得有些愚钝。我总是感觉事情在我不留神的时候就发生了,或者,也许在事情悄然发生的时候我总是在眺望着远方,眺望着我人生地平线上有些自己坚信会出现的东西。
今天,我重新拿起书架上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拍下两面“我”初见胖女郎的描写给@研冰看。这本书,自从高中读过两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动它了。在我所读过的村上春树中,它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大学两年,它一直被摆在书架上没有被翻开。高中的时候曾经给这本书写过一篇读后感,我大概是写道,这本书是可以被读很多遍的,每一次读,都能在里面的种种意象当中再找到点什么。事实上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人会处于一种潜入梦境和潜意识的状态,所以高中压力大的时候我在里面找到很多安慰。
今天我没有继续读下去。可能在某一个安静的下午我会再把它捧起来看,再一次从冷酷仙境的电梯厅和胖女郎一块下到夜鬼的巢穴,去找老博士和大脑的象厂切片;也再一次进入世界尽头的那座城,到档案馆里读刻在独角兽头骨里的梦,看它们经由我手逸散到大气中;最后我会吹起风笛,找到那女孩埋葬在苹果林里的心脏,然后任由我被割下的影子越过湖面,逃出这飞鸟也无法逾越的高墙。
P.S. 这一句写给我妈,我知道周报妈妈看得最多,这篇写得,乍一看云里雾里,但是咱们还是有个约定的,请妈妈看完之后不要想得太多。文字很像密电,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那本密码本,解出来多少就读多少,如果哪里看不懂,那一定不是写给你看的。
本周书摘
《反对阐释》已经看完,最后仅剩一篇预留的关于戈达尔的《随心所欲》的评论,《随心所欲》在洞头合宿的时候我没有认真看,所以这篇文章就不摘抄了。
反对阐释 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
过去数年间,就大约两世纪前随工业革命的来临而据说开始显露出来的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离这一问题,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根据这一诊断,任何有才智、头脑清晰的现代人,都只可能进入其中一种文化而排斥另一种文化。他所关切的,是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那些文献、技艺和问题;他说着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一种语言。最重要的是,掌握这两种文化所必备的那两类才具,具有巨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总体文化。它针对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人;它是奥特加·加塞特所定义的的那种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说的确切些,他提升着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即当一个人忘却了他所读过的一切而依然为他所拥有的那种文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科学文化是属于专家们的一种文化;它以记忆为基础,而要把握它,就要求全神贯注于理解。文学-艺术文化旨在内在化和吸收——换言之,是教化——而科学文化则旨在积累和外在化,即在用来解决问题的复杂工具和把握问题的特殊手段方面的积累和外在化。
……就众多文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言,他们对赋予现代社会以特征的那些变迁——其中主要的是工业化,以及每个人都体验到的工业化的那些后果,诸如规模巨大、毫无人情味儿的城市的激增,千篇一律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盛行,等等——有着一种历史的反感。工业化,即现代“科学”的产物,无论是依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模式,把它看作是毁坏自然并使生活标准化的机器轰鸣、烟雾弥漫的人工过程,还是依据那种更新的模式,把它看作是出现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那种清洁的、自动化的技术,都无关紧要。给出的评判都大体相同。痛感人性自身的状况正在面临新科学和新技术的威胁的文人们,憎恶这种变化,悲叹这种变化。但文人们不可避免地处在守势,无论是十九世纪的爱默生、梭罗、拉斯金,还是二十世纪那些把现代社会说成是一个新的难以理解的、“异化的”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深知,科学文化以及机器时代的来临不可遏止。
对两种文化这一问题的通常反应——这一议题的出现,比C·P·斯诺在数年前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就这一问题发表的那种粗糙、平庸的见解要早好几十年——是草率而浅薄地对艺术的功用进行一番辩护(使用的是“人道主义”这一更为含糊的意识形态词句),或仓促地把艺术的功用拱手让与科学。就第二种反应来说,我指的不是那些把艺术当作不精确、不真实之物、顶多不过是玩具而不予考虑的科学家(以及属于他们一派的那些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平庸论调。我指的是出现在那些热心投身于艺术的人们中间的那种严重的疑惑。有个性的艺术家在创造第一无二的艺术品以愉悦他人、培养其良知和感受力方面的作用,一再受到质疑。某些文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则走得更远,以至预言人的艺术创造行为终将消亡。艺术,在一个自动化的科学社会,将会丧失功用,变得毫无用处。
不过,我却认为,这种结论完全站不住脚。的确,在我看来,整个议题的表述似乎都失之粗糙。这是因为,“两种文化”这一问题假定科学和技术是变化的,是变动不居的,而艺术则是静止的,满足人类的某种永恒不变的普遍功用(慰藉?教化?消遣?)。只有基于这种错误的假定,人们才会推断出艺术即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的结论。
……
“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一个幻觉,是发生深刻的、令人困惑的历史变化的时代产生的一个暂时现象。我们所目睹的,与其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冲突,不如说是某种新的(具有潜在一致性的)感受力的创造。这终新感受力必然根植于我们的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对极端的社会流动性和身体流动性的体验,对人类所处环境的拥挤不堪(人口和物品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激增)的体验,对所能获取的诸如速度(身体的速度,如乘飞机旅行的情形;画面的速度,如电影中的情形)一类的新感觉的体验,对那种因艺术品的大规模再生产而成为可能的艺术的泛文化观点的体验。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艺术的消亡,而是艺术功能的一种转换。艺术最初出现于人类社会时是作为一种巫术-宗教活动,后来变成了描绘和评论世俗现实的一种技艺,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僭取了一种新的功用——既不是宗教的,也不起世俗化宗教的功用,也不仅是世俗的或渎神的(世俗的或渎神的这一概念,在其对立观念宗教的或神圣的变得过时之时,也就失效了)。艺术如今是一种新的工具,一种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而艺术的实践手段也获得了极大的拓展。的确,为应对艺术的这种新功用(这种新功用更多的是被感觉到的,而不是被清晰地系统表述出来的),艺术家不得不成为自觉的美学家:不断地对他们自己所使用的手段、材料和方法提出质疑。对取自“非艺术”领域——例如从工业技术,从商业的运作程序和意象,从纯粹私人的、主观的幻想和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占用和利用,似乎经常成了众多艺术家的首要的工作。画家们不再感到自己必须受制于画布和颜料,还可以采用头发、图片、胶水、沙子、自行车轮胎以及他们自己的牙刷和袜子。音乐家们不再拘泥于传统乐器的声音,而去使用改装的乐器以及合成声和工业噪声。
“高级”文化与“低级”(或“大众”、“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分,部分基于对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与大量生产的艺术品之间的差异的一种评价上。在一个大规模技术性再生产的时代,严肃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的价值,不过是因为这件作品独一无二,因为它带有他个人的个性的印记。大众文化(甚至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归于这一范畴)的作品之所以被看得一钱不值,是因为它们是被大量生产出来的物品,不带有个性的痕迹——是为那些没有多少个性特征的观众制作的大路货。但按照当代的艺术实践,这种区分看起来极为肤浅。近几十年来众多严肃的艺术作品具有明显无个性的特征。艺术作品重申自己作为“物品”的存在(甚至是作为大量制造或大量生产并吸收了大众艺术因素的物品),而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个人表达”的存在。
使文学获得突出地位的,是其肩负着“内容”的重荷,这既包括满篇的事实描写,又包括道德批判(正是这一点,才使英国和美国的大多数文学批评家能够把文学作品主要当作进行社会和文化诊断的文本、甚至是托词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专注于某部给定的小说或者剧作的那些作为艺术作品的属性)。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艺术实际上是那些内容要少得多、道德评判方式要冷静得多的艺术——如音乐、电影、舞蹈、建筑、绘画和雕刻。这些艺术的实践——它们全都大量地、自自然然地、不觉尴尬地吸纳科学和技术的因素——是新感受力的核心所在。
……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观念把艺术定义为对生活的一种批评——这被理解为提出道德、社会和政治诸多方面的思想来进行思考。新感受力却把艺术理解为对生活的一种拓展——这被理解为(新的)活力形式的再现。道德评价的作用在这里并未被否定,只是其范围被改变了;它变得不那么严厉,它在精确性和潜意识力量方面的所获弥补了它在话语明确性方面的损失。这是因为,比起我们储存在我们的脑袋里的那些思想储存物所塑造的我们,我们之本是甚至能更强烈、更深刻地去看(去听、去尝、去嗅、去感觉)。……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地是一个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改变(不论这种改变如何轻微)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义愤填膺的人道主义者们,务请留意。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当道德良知被理解为不过是人类的种种意识功能中的一种时候,艺术作品并没有停止其在人类意识中的存在。
感觉,情感,感受力的抽象形式与风格,全都具有价值。当代意识所诉诸的正是这些东西。当代艺术的基本单元不是思想,而是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或者,即便是“思想”,也是关于感受力形式的思想)。
……意识到以下这一点,颇为重要,即人类的感性意识不仅具有一种生物学本质,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每一种文化都会看重某些感觉,而抑制其他的感觉(对人类一些重要的情感来说,情形也是如此)。这种历史,正是艺术(还包括其他东西)进入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时代最引人入胜的艺术对其产生这样一种痛苦和危机的感受的原因,无论这种艺术以怎样游戏、抽象、明显价值中立的面目出现。
……现代艺术的严肃性排除了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快感——人们离开音乐厅后还能哼得出的某段旋律带来的那种快感,人们能够识别、认同并按现实主义心理动机加以剖析的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人物带来的那种快感。如果享乐主义指的是保持我们在艺术中发现快感的那些传统方式(传统的感觉形式和心理形式),那么新艺术是反享乐主义的。它使人们的感觉受到挑战,或给感觉造成痛苦。新的严肃音乐刺痛人们的耳朵,新绘画也不娱人眼目,新电影和少数令人感兴趣的新散体文学作品则难以看下去。对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或贝克特、巴勒斯的叙事作品的通常的抱怨是它们难以看懂或者难以卒读,它们“乏味”。然而指责其乏味,其实出自虚伪。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乏味这种东西。乏味只是某一类气馁感的别名而已。我们时代的那些引人入胜的艺术所说的那种新语言令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感受力气馁。
然而,艺术的目的终究总是提供快感——尽管我们的感受力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赶得上艺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提供的那种快感的形式。同样,人们也可以说,现代感受力抵消了当代严肃艺术的表面的反享乐主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涉及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快感。这是因为,新感受力要求艺术具有更少的“内容”,更加关注“形式”和风格的快感,它也不那么势利,不那么道学气——就其并不要求艺术中的快感必须与教益联系在一起而言。如果艺术被理解为情感的一种训导或者感觉的一种引导的话,那么劳森贝格的一幅画所带来的感觉(或感受)就与“至尊演唱组”的一支歌曲所产生的感觉没有什么差别了。……
……众多更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流行艺术的那种喜爱之情并不是一种新的平庸作风(如人们常常指责的那样),或某一类型的反智主义,或对文化的某种放弃行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美国众多最严肃的画家同样也是流行音乐中的“新声音”的着迷者,这一事实并非寻求消遣或者放松所致;例如,它与勋伯格也玩玩网球不一样。它反映了一种新的、更开放的看待我们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万物的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弃所有的标准:有大量的愚蠢的流行音乐,也有低劣的、装模作样的“先锋派”绘画、电影和音乐。关键之处在于,有着一些新标准,关于美、风格和趣味的新标准。新感受力是多元的;它既致力于一种令人苦恼的严肃性,又致力于乐趣、机智和怀旧。它也极有历史意识;其贪婪的兴趣(以及这些兴趣的变换)来得非常快,而且非常活跃。从这种新感受力的观点看,一部机器的美、解决一个数学难题的美、雅斯贝·约翰斯的某幅画作的美、让-吕克·戈达尔的某部影片的美以及披头士的个性和音乐的美,全都可以同等接纳。
反对阐释 后记:三十年后……
回头去看三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的作品,并非易事。我的那种作为作家的能量驱使我往前看,使我感到自己现如今才刚刚起步,真的才刚刚起步,这使我难以心平气和地面对当初的那个我,一个名符其实的初出茅庐的作家。
……
我是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还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离的道德家。我并不打算去写太多的宣言,但是我对格言表达方式的不可抑制的偏爱,有时却令我大吃一惊地与那些针锋相对的目标不谋而合。
……
我写作这些文章时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因此也是文化终结的时代:如果没有利他主义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也许是对终结的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并不比三十年前那种认为我们站在文化和社会的一个伟大的、积极的转型时期的门槛上的观点更虚幻。不,这不是幻觉,我这样认为。
这并不是说六十年代已经遭到否定,异端精神已经遭到压制,成了强烈怀旧的对象,而是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甚嚣尘上的消费资本主义价值促进了——实际上是强加了——文化的混合、傲慢无礼的态度以及对快感的辩护,这些我以前曾提倡过,但出自十分不同的理由。离开一定的背景,就谈不上什么可取之处。……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想使这些边缘观点更容易被人接受,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倘若我对自己的时代有更好的了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或许会使我更加谨慎。可以不夸张地把这种东西称作整个文化中的一场巨变,是对价值的一次重估——对这一过程,可用许多名称表示。野蛮主义是表示这种取而代之的东西的一个名称。不过,还是让我们使用尼采的词句吧:我们已经进入、真的已经进入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
……我仍劝请读者不要忽视这些文章的写作年代的更大的充满崇敬氛围的语境——这得需要一些想象力才行。在那时,呼吁“艺术的色情学”,并不意味着要贬低批评智力的作用。称赞那是被屈尊俯就地称作“流行”文化的作品,并不意味着要合谋来否定高级文化及其复杂性。当我指责某种浅薄的道德观时,我是在以一种更警觉、不那么自鸣得意的严肃态度的名义。我那时不理解的是,严肃本身已经处于失去其在整个文化中的可信度的早期阶段,不理解我所欣赏的某些更为出格的艺术会强化轻浮的、仅仅是消费主义的出格行为。三十年后,严肃标准几乎悉数土崩瓦解,而占据优势的是这么一种文化,其最浅显易懂、最有说服力的价值来自于娱乐业。
……这些文章中所表达的对趣味的种种评判或许已经流行开来。但据以做出这些评判的价值却并没有流行开来。
@研冰说,我的文风,都开始向她靠拢了,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