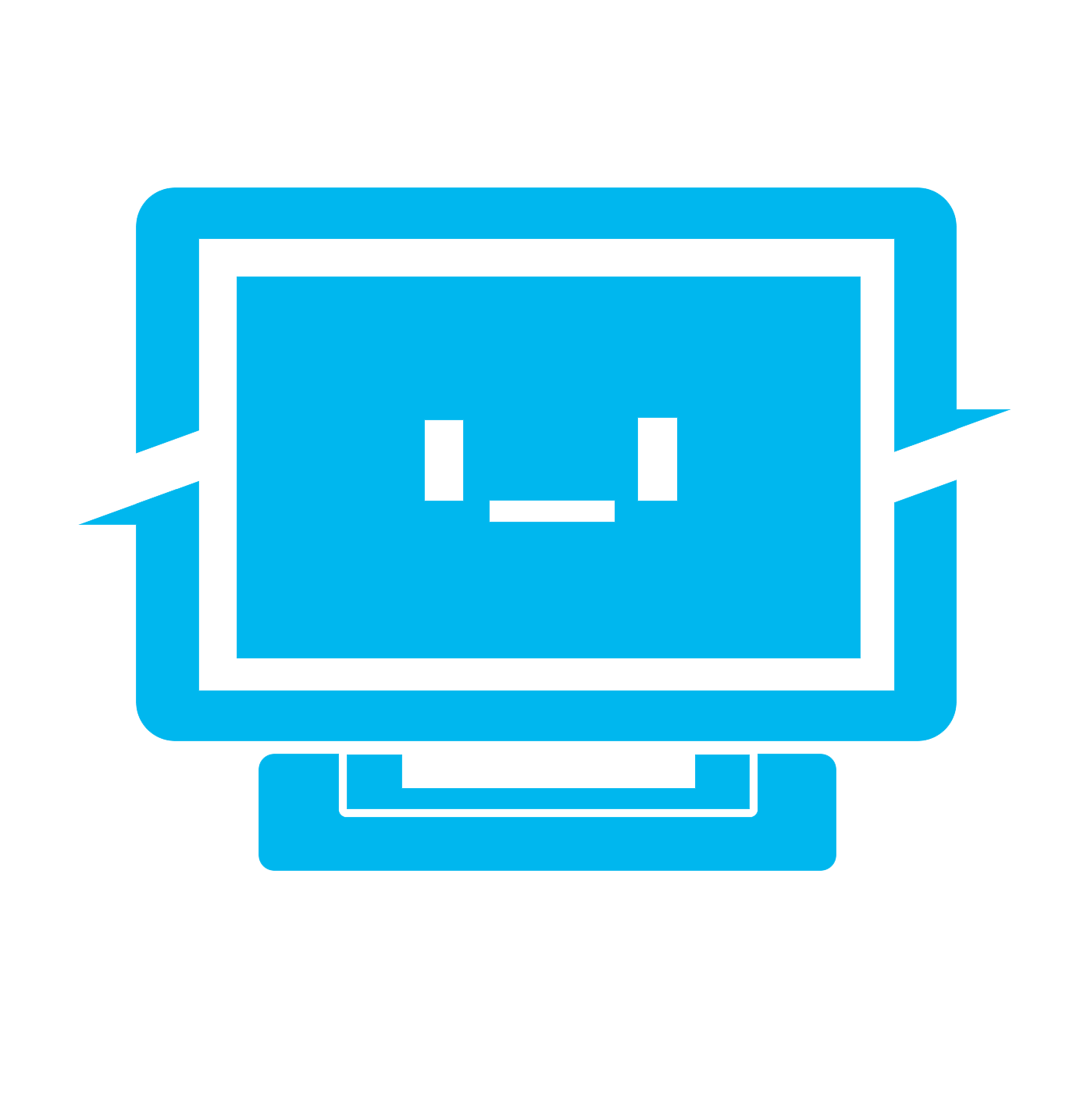暑假虽然漫长,但是时间流逝的速度是很快的。
各种事情的周期被拉伸得比较长,每天好像没干什么事情就过去了。不过一周往回头看一眼,也算是又做了一些事情,又学了些东西的。只不过这种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记的事情,无非是上了什么课,又看了哪些书,哪些网上的文,补了哪些番剧,收了哪些图,画了什么画。
有意思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件事是补了《命运石之门》这部galgame改的番剧。就像那些给我推荐的人说的那样,是一部神作。时空穿越然后逆天改命的故事是很老套的(放在这部番剧制作出来的2010年或许不算特别老套),但是既然是GalGame改编,人物塑造得是否让人喜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石头门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前面11集确实有些枯燥乏味,但对后面的剧情而言,前面11集撑开了故事的时间线,让事件能够更自然地填充进去,像是给后面留足空白。
一部作品是不是神作,去看它的同人圈子当前的产出就行。像“小圆”“石头门”“空之境界”“钢炼”这样的作品,就在前几天,我关注的很多不管是插画作者也好还是视频作者也好,都拿出了制作水准很高的作品(指的不是跟风,画师也好视频作者也好,为了关注度总是要跟风的,不过所谓制作水准高的二创作品,我更指的是对原作有特殊解读的作品,举些例子比如说亚亚子画的小圆,对Fate吉尔加美什故事重绘的手书“乌鲁克仍存于此”,Animenz的各种钢琴改编等等)。而这些作品完结距今已经过去八年、十年甚至更久。
另一件事情是打游戏,玩APEX,打单人排位赛打到黄金段位,然后卸载游戏。这个游戏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一个网络游戏。它的美术风格,UI界面,交互机制以及它自己的游戏文化圈各方面都不能单纯用‘好“这样一个词来描述,而是用”独特“更为合适。最大的感受是这个游戏你不需要语音交流也可以玩的跟有交流一样(指队伍信息标记功能太智能了)。
然后给我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和我曾经玩LOL不同,这个游戏里面的交流氛围没有掉到某种恶臭的圈子里。我是单人排位玩家,每局匹配到的都是陌生人。以前在LOL里面玩的时候(还有有段时间为了社交玩王者荣耀),经常遇到喷队友或者消极比赛的情况。玩家们很多时候的”临时仇恨“不在对手身上,而在玩不太好的队友身上。我有点想不明白APEX这个游戏为什么能够让陌生人如此团结而不是像我之前碰到的那些经常喷队友的情况。有的时候确实是技术不如对手,在对战中第一个倒下,但是一般不是重大战术错误,队友也不会怪罪你,更没有出现那种打个游戏就要问候你祖宗十八代的情况。三个陌生人一开麦,也能聊得没有什么阻碍,战术战略都能沟通上,打的好了就会收到队友由衷的赞美,有失误的时候,老玩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还有鼓励。
在B站上看到一个视频,”在日服体验真正的黄金精神“,在那局比赛里,3小队早早被打成仅剩1人,但是留下的这个人耐心地躲藏,在被围堵的时候没有放弃,最终找准机会复活队友,在决战中取得胜利。
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会觉得是什么让电子竞技能够称得上是竞技,而不是反对电子竞技的人说是”网瘾“的糖衣。我觉得它是有体育精神在的。就像打篮球的时候,如果你自私地想一个人打进攻,你很可能丢球,但如果你学会如何传球,团队的配合就会填补一个人无法达到的水平。而和体育一样,这一切又是建立在所有人个人技巧的普遍提升上。
和竞技体育(或者说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如果你希望玩的好,玩得转,想要技高人一筹,想要提升能力而不只是为了娱乐,你就需要练习,需要枯燥漫长的练习,练习射击练习跑动练习配合。看到那些大主播的射击水准,几乎和开了自动瞄准的外挂没有什么区别。很多时候,虽然APEX的高端局里面外挂不少,但是这些主播的小队经常利用地形、游戏机制还有对方的轻敌心理完成击杀外挂小队的壮举。
网络游戏的最本质的属性还是一种社交行为。所以如果说在这几天的游戏里什么让我觉得最开心,我觉得应该是每一局和我开麦聊天的陌生队友,听到刚开始的时候那一句句”哈喽哈喽!兄弟们开麦开麦!“,打赢比赛的时候“Nice!牛逼牛逼!”,还有在对战中激烈的交流,共享信息,告诉队友自己需要什么,并主动帮助队友。
大概这就是电子竞技的内涵吧。
本周周报就和之前的一样,下面以书摘为主。
卡尔维诺的名言两次在聊天中出现,主要是因为他写得实在切中肯綮。说起来,《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还没看,《看不见的城市》想看也还没看。
阅读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书本,不是来自作者,不是来自约定俗成的文字而是来自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来自客观世界中尚未表达出来而且尚无合适的词语表达的部分。——《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人到生命的某一时刻,他认识的人当中死去的会多过活着的。这时,你会拒绝接受其他面孔和其他表情:你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印着旧模子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佩戴了相应的面具。——《看不见的城市》
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真的啃了很久很久,几个月了,还是没有看完,现在看到大概70%左右(而且还跳过了很多篇文章)。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桑塔格的文学评论集子,很多时候我必须要先放下这本书去看看原著才能知道她在写些什么,比《激进意志的样式》要难读很多。你必须对当时的文艺界有所了解,必须去看看当时的电影(比如说戈达尔等新浪潮导演的电影,比如说罗伯特·布勒松的电影)。也正是从这这本书开始我才了解到电影作为文艺载体的那一些部分。也真正感受如同小说作品一般,大众电影和文艺电影究竟有什么不同。
下面的都是《反对阐释》的书摘。
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
然而,《热带的忧郁》之伟大,并不仅在于这种目光敏锐的报道,而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身体艰辛的意义,反思着新旧世界的城市,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的钥匙是第六章《我怎样成为了人类学家》,在这一章里,列维-斯特劳斯从自己的选择史中发现了一个案例,以此来研究人类学家们容易屈从的一种特别的精神危险。《热带的忧郁》是一部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书。像蒙田的《随笔》和弗洛伊德的《释梦》一样,它是一部精神自传,一部堪称典范的个人史,其中详尽阐明了对人类处境、全部感受性的整体看法。
纳塔丽·萨洛特与小说
一种新形式的说教占据了诸类艺术,它的确是艺术中的“现代”因素。其核心信条是这一种观念,即艺术必须发展。其成果是这一类作品,其主旨是要推动体裁的历史,在技巧上开拓创新。“前卫”和“后卫”这些准军事意象充分表达了这种新的说教作风。艺术是这么一支军队,人类的感受力借助更新的和更令人惊叹的技巧,跟随它义无反顾地走向未来。个人才能与传统之间这种主要表现为否定的关系,导致每一项新技巧、每一种新材料的使用走马灯似的迅速内在淘汰,它击败了把艺术当作带来喜闻乐见的快感的东西的艺术观念,产生了大量的主要是说教性和告诫性的作品。正如当今众所周知的那样,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的要旨不是去再现什么,更不是去再现一个下楼梯的裸女,而是要就自然形式何以能够碎裂成一系列的运动平面给我们上一课。斯坦因和贝克特的散体作品的要旨是要展示词法、标点法、句法和叙述秩序如何能够被重新调整,以表达意识的连续的出窍状态。韦伯和布莱兹的音乐的要旨是要显示——举例来说——沉默的韵律功能以及音色的结构性功能如何能够被改进。
……
我们将保留奇形怪状的小说残骸,像那些被置于风景中的报废的坦克。《芬尼根守灵夜》是一个例子,也许是最伟大的例子——它大体上没被读过,也不可读,被扔给了那些学究气的评注家来料理,他们或许能够给我们解读这本书,但不能告诉我们为何要读这本书或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如果乔伊斯指望他的读者把一辈子光阴都耗在他的这本书上,那似乎是一个极端无礼的要求;但考虑到他的著作独一无二,这又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乔伊斯这部封笔之作的命运,预示了它在英语文学中的一大批不像它那样庞大却同样缺乏情节的后继者的迟缓的接受状况——我想到了斯坦因、贝克特、巴勒斯等人的作品。难怪它们像是一些孤零零的突袭,在平静得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场上显得尤为突出。
……
萨洛特反对现实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现实并不是如此清楚明白的;生活并不是如此栩栩如生的。大多数小说中的逼真性所引起的那种不假思索、对号入座的现实感,是令人怀疑的,也应该被怀疑(的确,恰如萨洛特所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是怀疑。或者,如果怀疑不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的话,那至少也是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恶习)。
……
萨洛特所倡导的,是一种用连续不断的独白写成的小说,其中人物对话只是独白的功能延伸,而“真实的”言语只是无声的言语的继续。她把这种对话称为“潜对话”。就作者不进行干预或解释这个方面而言,它与戏剧对话相当,但与戏剧对话不同的是,它是连绵不断的,或它并不分派给显然可以分开的那些人物(萨洛特对那种点缀于大多数小说的字里行间的老掉牙的惯例,如
他说,她答道,某某宣布
等等,特别有一些尖刻、嘲弄的话要说)。对话必须“随着那些推动和扩展对话的小小的内在运动而变得活跃、膨胀起来”。小说必须否弃传统的心理描写手段——所谓反省,转而以浸没在对话里来展开小说。它必须把读者投入“那源源不断的内心深处的戏剧之流里,对这内在之流,连普鲁斯特也只来得及短暂地、空泛地瞥上一眼,他观察到的和再现出来的,只是一个浩淼的静止的轮廓”。小说必须不带评论地记录小说家的“我”所体验的与人和物的直接的、纯感觉的接触。小说必须全然放弃制造逼真性(萨洛特把它转让给电影),保留和增加“对体验行动的人来说行动自身所拥有的不确定的、不透明和神秘的因素”。
论《代表》
现时代最大的悲剧性事件,是六百万欧洲犹太人被屠杀。在一个不缺少悲剧的时代,这一事件最应该享有那种不值得羡慕的荣誉——因为它具有巨大的数量、单一的主题、丰富的历史意义以及纯粹的愚蠢这些特点.这是因为,没有人能理解这一事件。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不能全然以个人的或公共的狂热来加以解释,也不能以恐惧、疯狂、道德堕落或势不可挡,难以抗拒之社会力量来加以解释。二十多年后,围绕这一事件发生的争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怎么会允许发生这种事?谁为此负责?这个大事件是一个不能愈合的伤口;甚至理智的膏药都无济于事。
但即使我们知道得更多,也还不够。当我们说这个事件是“悲剧性的”时,我们就不仅仅是在要求一种事实的、历史的理解。说到悲剧,我指的是一个极度唤起怜悯和恐惧的事件,它的起因颇为复杂,多种多样,并且它具有一种警示或者启迪的性质,使幸存者负有严肃的责任来正视它。消化它。我们在把六百万犹太人的被屠杀称为悲剧时,是在承认在理智的理解(了解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或道德的理解(抓捕战争犯,把他们送上法庭)之外,另有一个动机。我们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事件是不可理解的。最终,惟一的反应仍是把这个事件继续放在内心,没齿不忘。然而承担记忆之负担的能力并不总是能胜任的。有时记忆会缓和悲痛或内疚;有时记忆却使悲痛或内疚更甚。最经常的情形是,记忆不能带来任何益处。然而我们感到记住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是合适的,或是恰当的。以及的这种道德作用跨越了知识、行动和艺术这些不同的世界。
我们生活在悲剧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一种历史形式的时代。戏剧家们不再去写作悲剧。但我们的确拥有反映或者试图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历史悲剧的艺术作品(尽管它们经常不被认作艺术作品)。在当今时代为此目的而发明出来或获得完善的那些不被认作艺术形式的东西中,可以列出精神分析会议、议会辩论、政治集会以及政治审判。由于现时代最大的悲剧性事件是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因此过去十年间最使人感兴趣、最使人激动的艺术作品之一,是一九六一年阿多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受审。
……
对正当程序(这场审判所诉诸的程序)的那种现代意识,无疑不是装出来的,但剧场与法庭之间古老的联系更为深刻。法庭审判显然是一种戏剧形式(实际上,历史上对法庭审判的最早描绘来自于戏剧——见之于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奥瑞斯忒亚》的第三部《报仇神》)。既然法庭审判显然是一种戏剧形式,那么剧场就是一个法庭。古典的戏剧形式常常表现为主角与反角之间的较量;而剧本提供的裁决是对行为的“判定”。所有的舞台悲剧都采用了这种审判主角的形式——这种悲剧形式的审判的独特之处是主角可能输掉官司(这就是说,遭谴责、受难、死亡),但也可能以某种方式打赢官司。
对灾难的想象
当然,与科幻小说比起来,根据科幻小说改编而成的科幻电影具有独到的优势,其中之一是对不同寻常之物或场面的直接呈现:例如身体畸形或异变,导弹和火箭之战,摩天大楼的倾塌,等等。而科幻电影的弱项,自然正是科幻小说的长项——我指的是科学方面。但科幻电影虽不提供一种智能方面的训练,却能提供科幻小说永远也无法提供的一种东西——详尽的直感。在电影中,人们靠画面和声音,而不是靠不得不通过想象力进行转换的文字,来参与到经历他自身的死亡以及城市的毁灭、人类自身的消亡的幻觉中。
科幻电影不是关于科学的,而是关于灾难的,此乃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之一。在科幻电影中,灾难很少表现为集中于某处;它常常是蔓延各处的。它是一个数量问题,一个捉摸不定的问题。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是一个规模问题。但这种规模,尤其是在彩色宽荧幕电影(在这些影片中,日本导演本多猪四郎和美国导演乔治·帕尔拍摄的影片从技术上说最有说服力,从视觉上说最令人激动)中,把问题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
因此,科幻电影(如同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当代体裁,即“事件剧”)关切的是毁灭的美学,是在毁灭的创造和混乱的制造中发现的独特的美。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的精髓正在于毁灭的意象中。……
这种大灾难幻象的诱惑力在于,它使人们从通常的义务中摆脱出来。……
这些影片提供的另一种能够带来满足的东西,是道德上极端的简单化——这就是说,是一个在道德上可接受下来的幻象,人们可以从中发泄残酷的或至少是不道德的情感。在这方面,科幻电影和恐怖电影部分地重合在了一起。……在来自于外太空的魔鬼形象中,畸形、丑陋和破坏性这些东西全都汇聚在了一起——它们为那种自以为正义在握的好战力量发泄自己提供了一个幻象靶子,为苦难和灾难的审美愉悦提供了一个幻想对象。科幻电影是最纯粹的景观之一;这就是说,我们几乎不进入他人的感受。我们只不过是看客,我们看看而已。
……
但与此同时,科幻电影的好战倾向被巧妙地导入了对和平的企盼,或至少是对和平共存的企盼。有的科学家总体上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即只有当地球遭受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地球上彼此打来打去的那些国家才会逐渐意识到共同的险境,从而搁置自己的冲突。……
科学——技术——被设想为伟大的联合者。因此,科幻电影也反映出一种乌托邦幻觉。……在这些社会里,理智取得了对情感的牢不可破的优势。因为所有的分歧或社会冲突在理智上都站不住脚,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理智的全面统治意味着全面的共识。同样有趣的是,这些被描绘成理智占全面优势的社会,也被传统地描绘成实践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或物质上简朴、经济上简单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但在科幻电影所展望的那种乌托邦世界共同体中,一切屈从于、受制于科学共识,在这里要求什么物质生存方面的简单性,将是荒谬的。
……
有这么一种感觉,认为所有这些影片都与恶势力有某种共谋关系。如我所说过的,它们使它中立化了。或许,这不过是一切艺术都在使用的把观赏者吸引进与它所再现之物的共谋关系中的方法。但在这些影片中,我们不得不与某些(实际上)不可思议的东西共处。这里,“思考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不是以赫尔曼·卡恩的那种方式,将其作为预测的对象,而是作为幻想的对象——不论如何漫不经心,从道德的角度看,本身都成了一种或多或少成问题的行为。这些电影把有关身份认同、意志选择、力量、知识、幸福、社会共识、罪恶、责任等对我们当前的极端状况无济于事的那些陈词滥调全都永恒化了。但要祛除那些集体梦魇,不能靠展示它们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虚妄性。这种梦魇——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于科幻电影中的那种梦魇——与我们的现实离得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