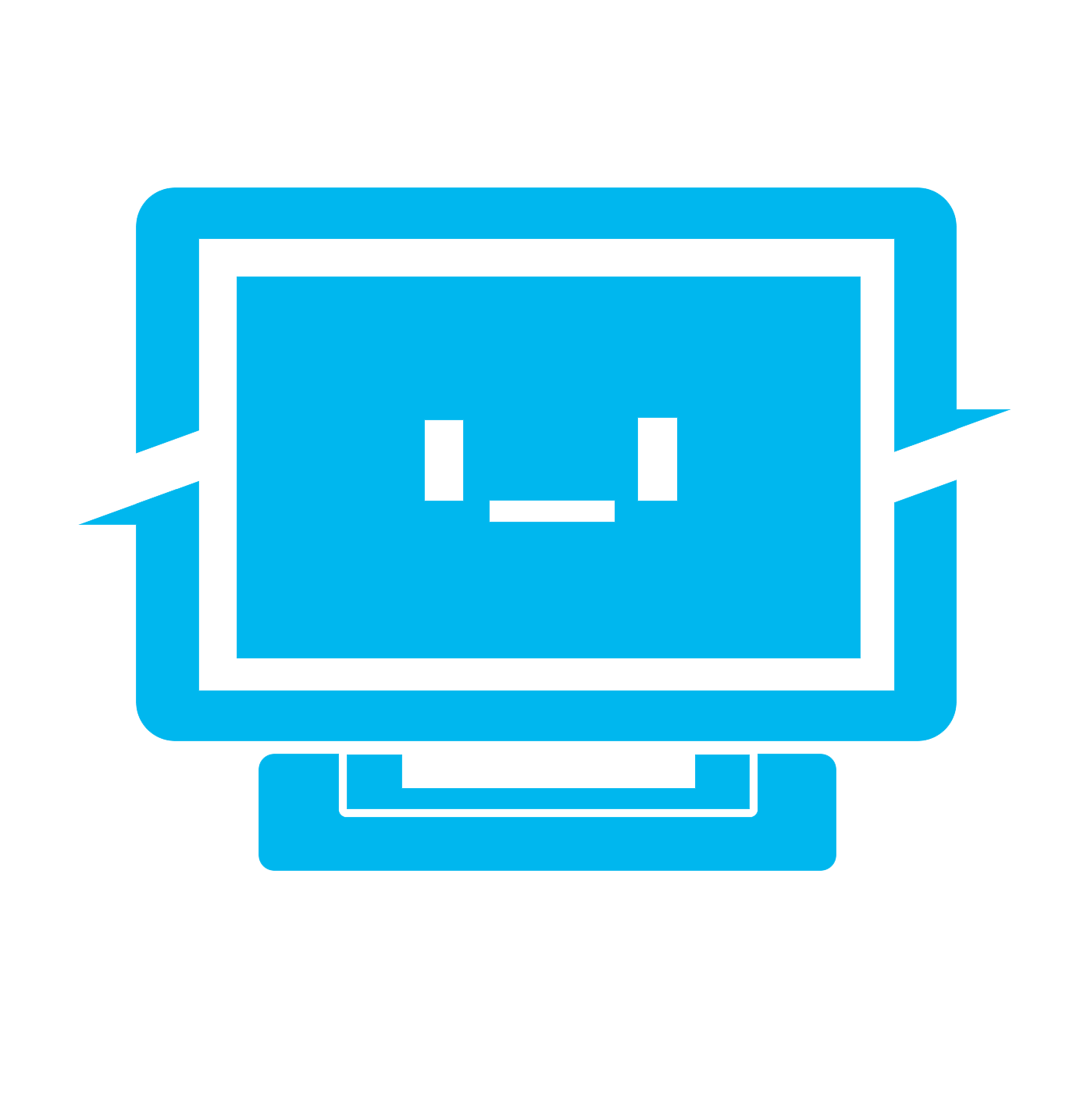重庆
大学两年来,可能这一次旅游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返程前一天,大家都在说舍不得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过,从飞机落地杭州那一刻开始,一些空虚感逐渐抓住了我。当然这很可能是愉快的旅游结束后心理上的强烈落差。我只觉得,杭州,这个我待了两年的城市,忽然变得有些陌生。它变得有点过分安静。也正是我在摇晃的地铁里昏昏欲睡在炎炎正午拖着行李箱转乘公交车到隔离宾馆的时候,思绪开始整理关于重庆的种种细节。
山城给我的第一印象并非火锅,而是建筑。虽然浙江多丘陵,但从未有过哪个城市会把无数高耸的摩天大楼高密度地建在山上。在我去过的城市里,无论是上海、杭州、苏州还是北京、南京,平原地区的城市有一种疏离感。而重庆并不是,或许本身可以修建房屋的地方并不多,所以它反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立体空间。重庆有很多盘旋而上的单行道和双向单车道,相比于平原大城市常见的双向双车道,重庆的道路是逼仄的。大概是为了保护重庆人的膝盖,这里看不到共享单车。
依山而建的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重庆的道路构成的迷宫,是在立体维度上展开的。一幢大厦的22层,其实是另一些大厦的1楼。似乎是为了统一参考标准,重庆的同学总是以临江大道上的店面作为第一层。
复杂的垂直落差关系有时候会造成某种错觉。在路面上行走的时候,随处可见从一个平面连接到另一个平面的阶梯和走道,而这些走道,更像是这个城市隐秘的一面。路面之上的,是无数综合体、商场、金融中心和摩天大楼,而在路面之下,则随处可见苍蝇馆子、路边摊和批发市场。垂直落差将这个城市包裹起来,如同将一张白纸揉皱成球。与单位水平面积中立体面积一起增加的,还有这个城市存储信息的容量。在白象居的楼栋间穿行的时候,我对同行的同学说:“重庆是一个可以容纳很多故事和秘密的城市。”这也难怪像《隐秘的角落》《少年的你》这些有些悬疑成分的作品会在重庆取景。
立体关系的丰富给这个城市很强的层次感。不管是临江的大道还是楼间的小巷,到处都有可以取景摄影的机位。山势天然为摄影者提供了高空的取景点,你不需要使用无人机、不需要爬楼,仅仅站在不同海拔的平面上,就可以从楼房的中段而不是底部拍摄。也正因此,重庆的江面不比温州的瓯江或者上海的黄浦江宽阔,但在包含两江的照片里,这个城市的风格是开阔的。在一张照片里,几乎不需要为大楼之间的遮挡关系苦恼,就像是影院或者剧院逐层增高的后排座位一样,你总能将前后的高楼都放入取景框。
重庆的热闹给人一种现代商业和传统烟火气的结合之感。这大概和这个城市的地理也有些关系。由于偏西部的位置和夏天的长日照,重庆的日落时间非常靠后。这里的太阳八点钟才下山,而要到十点多,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夜晚的重庆我觉得是最贴近银翼杀手里面赛博城市的三次元城市。
大厦在逼仄的道路里尤其显得高耸,地表之下的市井摊贩和地表之上的大型商场则正好对应了赛博朋克世界里无数的小店和大公司。闹市区的高度集中也让重庆的人流密度变得很大,有时候明明也没有什么人,但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拥挤之感。我们到重庆的第一个晚上下了点雨,透明伞加上街边悬挂的LED广告牌,特别有《银翼杀手2001》最开头雨夜的感觉。
夜晚在这里似乎被整体延后的两个小时,人们似乎都在凌晨入睡,而白天则照常由开早餐店的人们在三四点钟开启。在重庆的大街上,熬夜和通宵似乎变得异常容易。
重庆的休闲和苏州的休闲有些不同。苏州的休闲更安静而重庆则带有更多的躁动。同样是金鸡湖边上的世纪中心和大型综合体,苏州并没有让人感觉到紧迫,苏州的风格如同茶水,醇厚或者清淡,总归是慢悠悠的;而重庆的风格有点像火锅,红汤沸腾,虽然是在娱乐休闲,但会让人神经紧绷。
山城的食物,我的嘴巴很喜欢,但我的肠胃属实不太适应。
麻辣不是重点,油大才是。毕竟辣只是对舌尖的考验,最多在吃饭的一个小时里,而油,则让我孱弱的肠道不得不24小时全天候高强度工作。第一顿饭吃的就是纯麻辣的九宫格火锅,嘴巴吃嗨了,放下筷子人差点没能从座位上站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8个小时不吃任何东西也能感受到的肠胃压力。老妈往箱子里塞了降火的“清开灵”和缓解肠胃压力的“午时茶”,在重庆上火其实不容易,但“午时茶”确实是在第一天起到了很大作用。
后面几天我们吃得就收敛了很多,吃点软和的大米,吃点面食(虽然重庆小面和肥肠面都是完全的红汤红油),而少一些不带主食的火锅串串。
说起来,来重庆让我改变了对有一道菜的印象,这道菜叫烤脑花。最开始是在《人生一串》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的,可能受一些以往的观念的影响,脑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存在着心理上的或多或少的障碍。我第一次真正吃脑花是在浙大堕落街的“付小姐在成都”,不过因为当时脑花放凉了,并且配的料不太行,脑花的腥膻并没有去净,而其鲜香也就没有真正被释放出来。
这次吃到的脑花几乎与荤的豆腐无异,并且更加黏滑有弹性,烤脑花用的汤汁看着很红,但其实不辣不油。
另外吃了冰粉、凉虾(竟然是素的)、冰汤圆和毛血旺、钵钵鸡、串串、香辣小龙虾、酱油鸡、回锅肉、鱼香肉丝、各类肥肠。
网络时代的旅游格调和十年前的旅游格调已经不同了。因为可以轻易地捧红一个地标或者店铺,在旅行者到达那里之前,就已经看过无数它的照片和视频,听过无数博主对它的描述了。奇景在手机摄像头和麦克风下褪去了原先神话的外衣,而变成了网路世界的形状。在尚未到达的旅者眼里,这些景点早已祛魅。
就像是去李子坝的穿楼地铁那一次一样,人们聚集在最前部的车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但事实上穿楼地铁也不过就是一个地铁站修在楼房里罢了,这幢楼也基本上完全就成了地铁站和商店本身。也难怪有人在下车前说:“在车里看列车穿楼而过没有在外面看的有味道。”
或许重要的是和你一块出行的那些人,你们的旅游观念、在旅游中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否相同。这一次,我们既没有在很紧的schedule里面疲于从一个目的地奔向另一个目的地(上次去苏州是这样的),也没有因为不知道去哪里或者完全无所谓去哪里,而在住宿的地方摆烂。我们以一种很自由的姿态在这个城市里穿行。或许是都在享受这种自由的状态,我们对去哪里从来没有分歧,一拍即合,说走就走,就像我们约起这一次旅行一样。相机没电了,或者临时有事了,我们就在最热的下午时分回到民宿,看一部新浪潮的电影,晚上再出门觅食。
没有特别固定的饭点和作息,早饭十一点吃,午饭两点吃,晚饭七点吃,最后再来点啤酒和水果作为夜宵,听着摇滚和后朋克的歌曲,一直聊天到深夜。
闲聊的时候,我更多作为一个倾听故事的人。通过听,我得以以一种浓缩的方式再去度过我的初高中,去重新经历那些我曾有过短暂交集而实际上浑然不知的事情,去重新认识那些或许只是我听说过的名字。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一些你曾经历过的事情,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另一面。而我长久以来明白,自己在学习或者工作的场合或许与人交集很深,而在此之外的关于社交与秘密的世界,我是处于边缘的一类人。借此,我或许可以稍稍地填补过去八年匮乏的公共社交生活。
就这样,在重庆度过的夜晚,就如同《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中所说的那样,每一个都如四季一般漫长。我算是明白了,欢乐的时光并不短暂:在这些充满着梗与欢笑,回忆和故事的夏夜良宵,时间似乎停止了流逝。
这是一次很纯粹的探寻。在拓展生活和生命的边界这一件事情上,我仅仅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新人。昨天和@研冰说起这件事,ta说我大概在某些程度上是一个割裂的人。好多时候我似乎只能在自己划定的空间里挖掘出一些东西,但是丢掉了尼采式的那种生命“强力”。很多时候,大环境并不向你许诺完美的条件,就像是高中上了竞赛这条船,大学又被疫情或者内卷所困,如同现在我们旅行结束,该去挂职的去挂职了,该去实习的去实习了,该在宾馆里隔离的还在隔离。我不再相信,“哦这里有个完美的毕业季”“这里有个完全空置的假期”,我会说,或许许多事情要先搁置一下,或许要支付一些代价,但我觉得值得。
本周书摘
“自我提升”:一门供需两旺的生意
“自我提升的潮流随时代而变化,旧导师们被新一代导师取代⋯⋯”赛德斯多罗姆和史派瑟写道,“唯一保持不变的是一种承诺:你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社会里,我们不会因为购买了一条牛仔裤而感到彻底的满足。同样,在自我提升的领域里,我们不会只期望提升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我们被鼓励立竿见影地全方位地升级我们的生活。我们理所应当变得更苗条、更健康、更幸福、更聪明、更平静、更有效率——迅速地、全天候地。一种压力产生了:人人都能通向完美生活。”
少年华盛顿砍掉了父亲钟爱的樱桃树,后来他主动向父亲认错,得到父亲的原谅和赞赏。这个故事的源头是牧师梅森·维姆斯(Mason Weems)在华盛顿去世之后不久创作的总统传记。维姆斯杜撰了少年华盛顿的事迹,以期望教导人们恪守诚实的品行。訾非说,这个故事包含了人生神话的产生所必需的条件:神话所附会的对象本身具有欲望符号的功能——“把‘谦虚诚实’这个美德附会在一位伟人身上,一定比附会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更能激起一种隐秘的愿望:如果我也具有这样的品质,那么我将来也能成为大人物”。
不论童话、教科书还是卡通故事里,诚实者总是得到了品德之外的好处——财富、地位、声望,甚至因此逃脱了死亡的考验。而假如一个道德家开诚布公地宣扬诚实:诚实并不总能得到好报,甚至诚实的人往往比不诚实的人吃亏,但我们仍然应该诚实,因为诚实是一种比获得好报更可贵的美德。很显然,这样的故事并不会有太多听众。200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热衷于用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教育孩子,因为孩子无法抗拒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但事实上,訾非说,就多数成年人来说,平凡的现实真相也绝不是他们乐于接受的东西。“神话尽管不真,但却是一种精神动力,为生活带来了某种意义。”
今天,价值观的多元、信息来源的爆炸、传播渠道的丰富使各种层次、各种内容的“神话”层出不穷。我们有白手起家的创业神话;有“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的分数神话;有亲子、情感、事业、个人样样出众的辣妈神话⋯⋯这些神话同样以世俗成功为诱惑,它们可能并不附会在一个伟人身上,但可能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它们暗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并且应当完美。
传统社会,阶层和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天花板,但现代社会,个体的可能性被无限放大。这既是自由与机遇,也是沉重和痛苦的负担。“只要努力就会成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神话。这句话既对人产生深刻的激励,也潜藏了巨大的否定:如果你没有能够达到某种期待和目标,一定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你对自己负有全权责任,你理应掌控一切。
反对阐释
加缪的《日记》
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众所周知,女人能够忍受情人的一些品性——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以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而当这些品性出现在丈夫身上时,她们绝不苟同。同样,读者可以忍受一个作家的不可理喻、纠缠不休、痛苦的真相、谎言和糟糕的语法——只要能获得补偿就行,那就是该作家能让他们体会到罕见的情感和危险的感受。在艺术中,正如在生活中,丈夫和情人不可或缺。当一个人被迫在他们之间做出取舍时,那真是天大的憾事。
同样在艺术中,犹如在生活中,情人不得不常常位居其次。在文学的繁盛时代,丈夫比情人为数更众;在所有的文学繁盛时代——这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倒错是现代文学的缪斯。如今,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丈夫们感到内疚,全都想去当情人。甚至像托马斯·曼这样如此有大丈夫气的、可敬的作家,也为对德性的一种暧昧态度所苦,并把这种暧昧的态度装扮成资产阶级与艺术家之间的冲突,唠叨个没完。
……
我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阿贝尔·加缪,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作为一个当代人,他不得不贩卖疯子们的主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不过,他这样做时,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至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他从流行的虚无主义的前提出发,然后——全靠了他镇静的声音和语调的力量——把他的读者带向那些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其前提得出来。这种虚无主义深渊向外的非逻辑的一跃,正是加缪何以唤起了读者一方的挚爱之情的原因。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如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
作家是受难者的典范,是因为他既发现了最深处的苦难,又有使他的苦难升华(就实际意义上而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升华而言)的职业性途径。作为一个人,他受难;作为一个作家,他把苦难转化成了艺术。作家是发现受难在艺术经济中的用处的人——正如圣徒们发现受难在救赎经济中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帕韦哲对情爱的思考,是我们所熟悉的浪漫主义理想化的另一面。如司汤达当初一样,帕韦哲再度发现爱情本质上是虚构;这并不是说爱情有时导致错误,而是爱情本质上就是一个错误。被人们当作是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之情的东西,揭去其伪装的话,其实是孤独自我的有一次舞蹈。容易看出这种情爱观如何特别适合现代作家的使命。在亚里士多德式的那种视艺术为模仿的传统看来,作家是一种媒介或传达手段,用来描绘他自身之外的东西的真相。在视艺术为自我表达的现代传统(大致说来,自卢梭已降)看来,艺术家叙说自己的真相。因此,那种把伪装成对所爱之人或物的价值的体验或揭示的情爱视作自我之体验或揭示的理论,势必只关乎情爱自身。情爱,正如艺术,成了自我表达的媒介。然而,由于结交一个女人不像创作一部小说或一首诗歌那样是个人独自的行为,它注定要失败。
……
现代对情爱关系的虚幻性深信不疑,导致了一个更深远的后果,即新出现的对那种得不到回报的情爱的无法回避的吸引力的一种自觉地默认。因为爱情是孤独自我所感受到的一种被误投到外部的情感,因而被爱之人的自我的不可征服性对浪漫主义想象力产生了一种催眠术般的吸引力。得不到回报的爱情之所以有诱惑力,在于它契合帕韦哲所说的“完美的行为”以及强大、孤绝和冷漠的自我。“完美的行为产生于彻底的冷漠。”帕韦哲在1940年的一阙日记中写道,“这或许就是我们常常疯狂地去爱对我们冷漠以待的人的原因;她代表了‘风格’,代表了令人着迷的‘品味’,代表了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