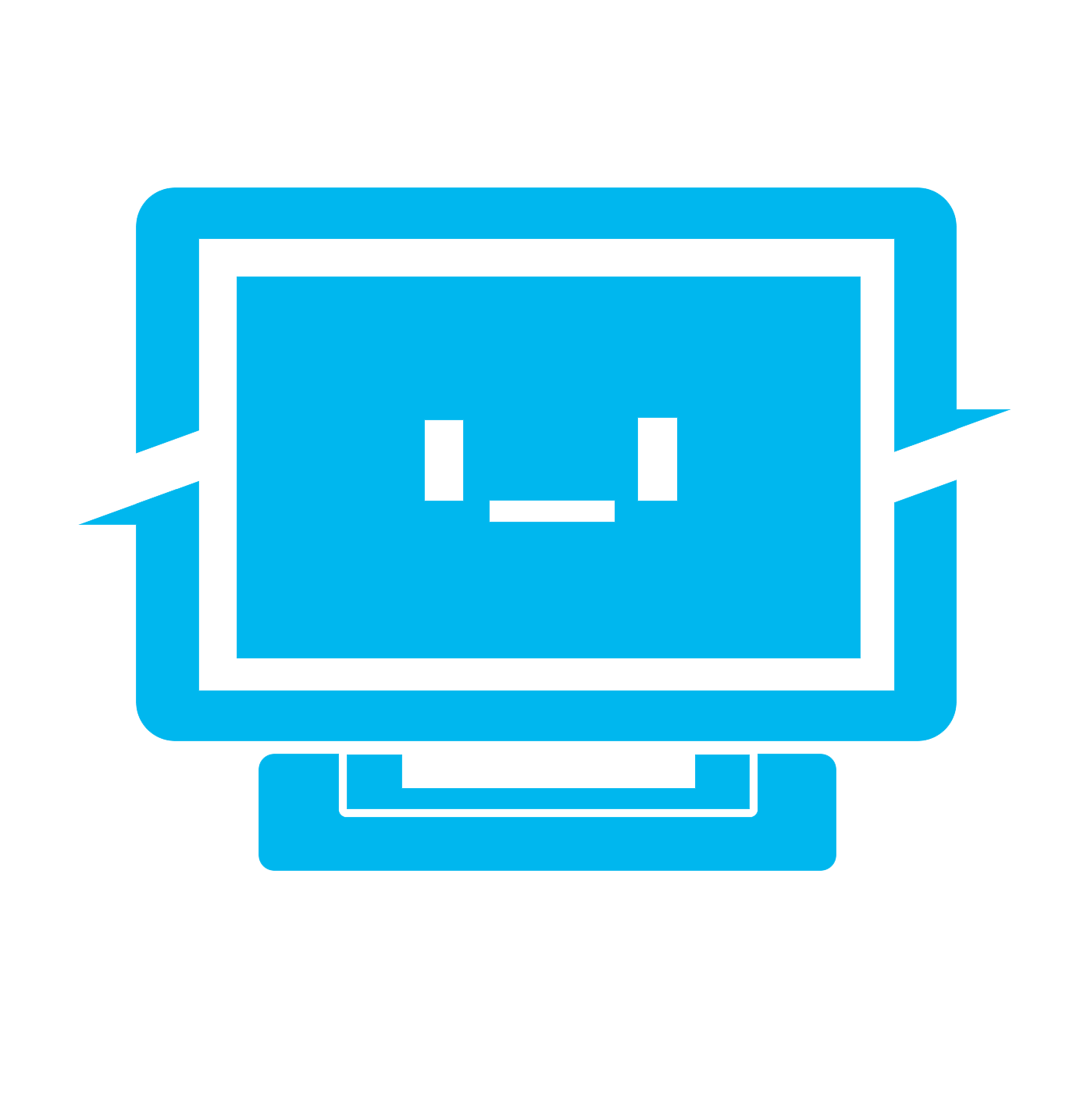A New Begin
旷日持久的考试周和更加折磨的考试月终于宣告结束。从5月10号第十九周周报之后,我的周报断更至今。其实在这样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还是有相当多的时刻,有过想要动手打字,写下一些什么东西的冲动。不过,写一篇周报的优先级,总归是排在了肝各种大作业以及相对需要的休息(睡觉、打游戏、听歌)之后了,绘画这种更加消耗时间的活动,在期中之后基本就没有进行了(我应该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画过一笔了)。
趁现在许多课都还没出分,我也好“客观”地评价一下这学期上的各门课程。先从已经出分的“无线电测向”和“随机过程”说起吧。“无线电测向”这门体育课我原先以为会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门课。因为积分赛的考试制度按排名现后次序计分,这就意味着考试并不是纯粹的技能熟练程度检测,而是带有比赛性质的。而这门体育课本身的技术难度不大,无非就是“定位”+“变速跑”的组合罢了。然而最后发现老师给出的分数还是相当的高,虽然大有骑车组队犯规的人,但最后比赛还是个人能力占据了主要矛盾(幸好对于黑箱来说比较)。选随机过程这门课主要是为了看懂后面的人工智能内容(事实上是上一个学期的“人工智能基础”介绍的众多内容,那个时候连会用都说不上,郑能干老师还讲了很多原理层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的“晦涩”),不过说实话这些基础的概率论东西实在是不足以真正看懂那些模型,但或多或少还是明白了一些基础的假设的出处。
然后是数据库和计算机组成,这两门课占据了本学期后半学期的七成的时间。很多人对这两门课的评价不是很高,就学到的知识而言,我还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两门课对我来说有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只有做完了实验才真正弄懂了理论课所讲的内容。这两门课的实验,做得实在是痛苦,阅读理解实验实现的要求和后期的Debug消耗了大量的时间,而真正敲打代码的时间竟成了开销最小的部分。除去正常的开发过程,平衡本就压力很大的小组成员之间的时间安排,还有把控整组的工程进度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做这些小组合作的实验的时候最大的体会是,分给你的工作量只是主要由你负责实现的代码部分,而不是你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只关注了他自己的部分的话,很容易造成在代码封装的过程中具体实现被“踢皮球”的乌龙事件。而且如果没有对其他人的工作有一个深入了解的话,甚至在自己调用底层或者自己被顶层调用时都会出现因为调用方式不对(或者调用的上下文和这个函数本来应该完成的事情不匹配)而产生BUG。
认知神经科学导论是一门讲座性质的课。上课的时候听起来都是好高端好前沿好抽象的东西,然后人一直处于没有学懂的情况。但是最后期末复习的时候仔细去理解去查了相关的资料,发现这门课所讲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而且基础的。唐华锦老师的十六节课化归到最后就是一个命题“教你如何从生物神经元模型推导出人工神经网络的种种结构”。这一门课也正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联结主义的人工智能仍然没有找到关键的突破口”,而人类还需要向生物和自然学习太多东西,或许曾经是仿生物的肢体结构骨骼构造,但现在要仿制的是最为精密的神经系统中枢。在对人脑机理的真正理解之前,再强模型对人脑的模仿都只能算是“拙劣”。
然后是高级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对于数学不好的学生而言简直是噩梦。只能说多谢老师的不杀之恩,还有队友的强力带飞。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大概是本学期众多专业课中唯一算的上是轻松的课了。做这门课的课程设计大概是本班同学在期末月的唯一娱乐项目了(笑)。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一门政治课。班里有熟读德国法国哲学原著的大佬对此门课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就学术而言讲歪了很多东西。不过,从小学到大学,这门思政课是我听得最舒服的一门思政课。至少就哲学那几个最基础的问题,吴旭平老师都做了相对专业的解说,而没有像其他的思政课一样陷入到泛滥的“赞歌”和不知所云的“批判”之中。也正因此,我才得以真正得知,马克思的那一套矛盾论,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究竟在实际事物上如何运用。而不是我直到“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两个词,但是什么是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完全由老师和题目答案说了算一样。也正因此,政治经济学内容是这门课最有意思的部分,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真正的一种应用,是真正可以从中看到经济和政治、国际关系等的一些基本规律的。它教你推导出这些规律,而不把结论夹带着没有意义的价值判断直接填鸭式地塞到学生的脑子里。吴旭平老师上这门课最好的一个部分在于他倡导着一种可以归于理想主义的三观。他所讲述的马克思主义,在倡导人进入封闭的体制之前,先倡导人的自我实现。他没有因为说集体高于个人那么个人就必须在任何问题上屈从所谓“集体”的意志。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那就必须让人的天性和才能充分释放。如果说他的哲学讲得并不是属于顶尖专业的话,他至少是一个足够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布道者。相比于那些对于这个学说充满麻木的吹捧与赞歌而在谈及个人实现时则要么转向世俗的功利主义、要么转向政治化的“号召”的思政老师来说,他是属于通透且真诚的那一类人,是真正能通过这门学科带给迷茫的大学生心理上一些安慰的人。
现在想想,近代史纲要能够由赵晖老师来上,军事理论能够由程春老师来上,马克思主义原理能够由吴旭平老师来上,真的是大学的一大幸运之事。
这篇周报的名字取名为A New Begin,大概是因为,大一大二两年过完,大学正式过半,而且暑期就要搬去其他校区了,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浙大待了两年之后,对大学生活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在经历课程压力、封城和显卡大幅溢价的“赛博封城”之后,能否在这个恶劣的内卷环境下找到一些归属感。有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前一代人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出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集体苦难而英雄的生产年代已经离我们而去,然而物质丰裕的伪像背后,是上升渠道的收窄,和整体意义的缺失。两年来我其实多次回望高考,回望这个不知道是让人获取了更多还是丢失了更多的有些残酷的竞争游戏。就像是很多人一到大学就会躺平乃至颓废,我想并非是因为电子游戏的诱惑力太大,而是因为对以往生活的完全拒绝。当社会,当旁观者,当他们的家长对他们的状态产生质疑而不是同情的时候,那一杆标尺也只能是功利的。有的人说,你应该把高考放下了。事实上,对于人生经历并不丰富的我来说,我所熟悉且想要逃离的,也不过就是这一个被人为安排好的“角斗游戏”罢了。这两天高考出分,热搜第一条是数学满分的学霸说自己喜欢打游戏。百度最近上新了一个非常垃圾的功能,叫做热搜弹幕评论,这无疑是你能看到的网络文化水平最低的评论区。就这件事情而言,人们更多表达自己的无奈,表达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享有“数学考满分”且“打游戏”这样的“成就”。但“数学考满分”,这又如何呢?人家打游戏,这又如何呢?我看到的不是他的分数和打游戏这个看似不能被忍受的爱好,而是他对自我的实现。在目前的我的观念里,“自我实现”是跳出功利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期望的太多了,完全没有思考“大学生活”这个伪命题背后的经济基础是否成立。也因此我并不再去把下一个十年的奋斗完全寄托于十年后赚的钱、地位高低之上。目标和理想的确立是为了让人在或许漫长,或许枯燥的学习工作中能够自我奖励,而不是自我牺牲。
最近有一些刚刚考完高考的同学来问我高考之后该做什么。事实上我都觉得这是他们家长让他们来问的。因为高考之后两个月该做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在或许是二十岁之前最为自由的两个月做的事,这种事情,我只能请你去问问自己的内心到底要干什么,要玩就去玩,想玩电脑玩手机的就去买一台来玩,要出去旅游的就去旅游。一定问我要学什么的,我强烈建议你不要碰大学英语、专业课程、大学数学,不要让后面这些仍然带有“高考印记”的东西侵入最为纯粹的两个月。
许多家长把打游戏和丧志划了等号。这其实并不怪他们,因为所有人都听过沉迷并且荒废的故事。然而,游戏不过是可以说最为安逸并且最为显性的人造乐园罢了。它终究是开发者为玩家构筑的庭院,而不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生。当人意识到它的有限性时,或许可以说,他就挣脱了这种有限性。我想到前阵子罗翔老师发了一段关于快乐的探讨,核心的观点有两句话:“越是高级的快乐,越能够发挥人的自主性”,以及“高级快乐能够理解低级快乐,而低级快乐难以理解高级快乐”。
有段时间我特别在意大学之后该出国还是保研。现在我学会把眼光再放远一点看,这种“远”不是把人生自由的希望丢到三十岁成家、四十岁立业、五十岁六十岁退休这些时间节点之后的那些“短暂”的可以被事物明显表征的自由,而是把目光平行地投向我的整个人生,甚至投向历史的尺度和世界的维度,这种目光要求我必须在每一个时刻都坚定地看向自己脚下所占的位置和未来,要同时对未来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负责,因为意义并非空洞堆砌,而必须由人去践行。
许久许久没有写过除了实验报告以外的文字,这篇周报写得可谓是艰难。估计自己的画技也已经损失大半了。今年以来发现学习任何东西都是熟能生巧,无论是学数学和计算机,还是学音乐还是学绘画,甚至是打游戏,只有不断的练习,把基本功练好了,水平才会有所提升。
考试周的一个晚上我复习间隙在图书馆起身于书架见闲逛。偶然摸到一本叶永烈写的《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个多小时马马虎虎翻完了。这本书从粉碎四人帮讲起,写到华国锋同志引退。读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每一种思想的转变都是要经历迷茫和阵痛的。一代人不能改变的思想,就要由两代人改变。政治书历史书上短短一句:“《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背后是最高领导层的政治震动,连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由来,都蕴藏着思想革命发动曾经接近失败的风险与危机。
下个学期将是我最为忙碌的一个学期,打算暑假开始提前学一些国外的平替网课了。即使很忙,最后的两学分通识我还是给了零基础钢琴课,虽然我得跨校区并且钢琴课之后的专业课必须线上上,但我觉得在为一个以及期待已久的艺术技能只用付出这些,已经属于赚翻了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