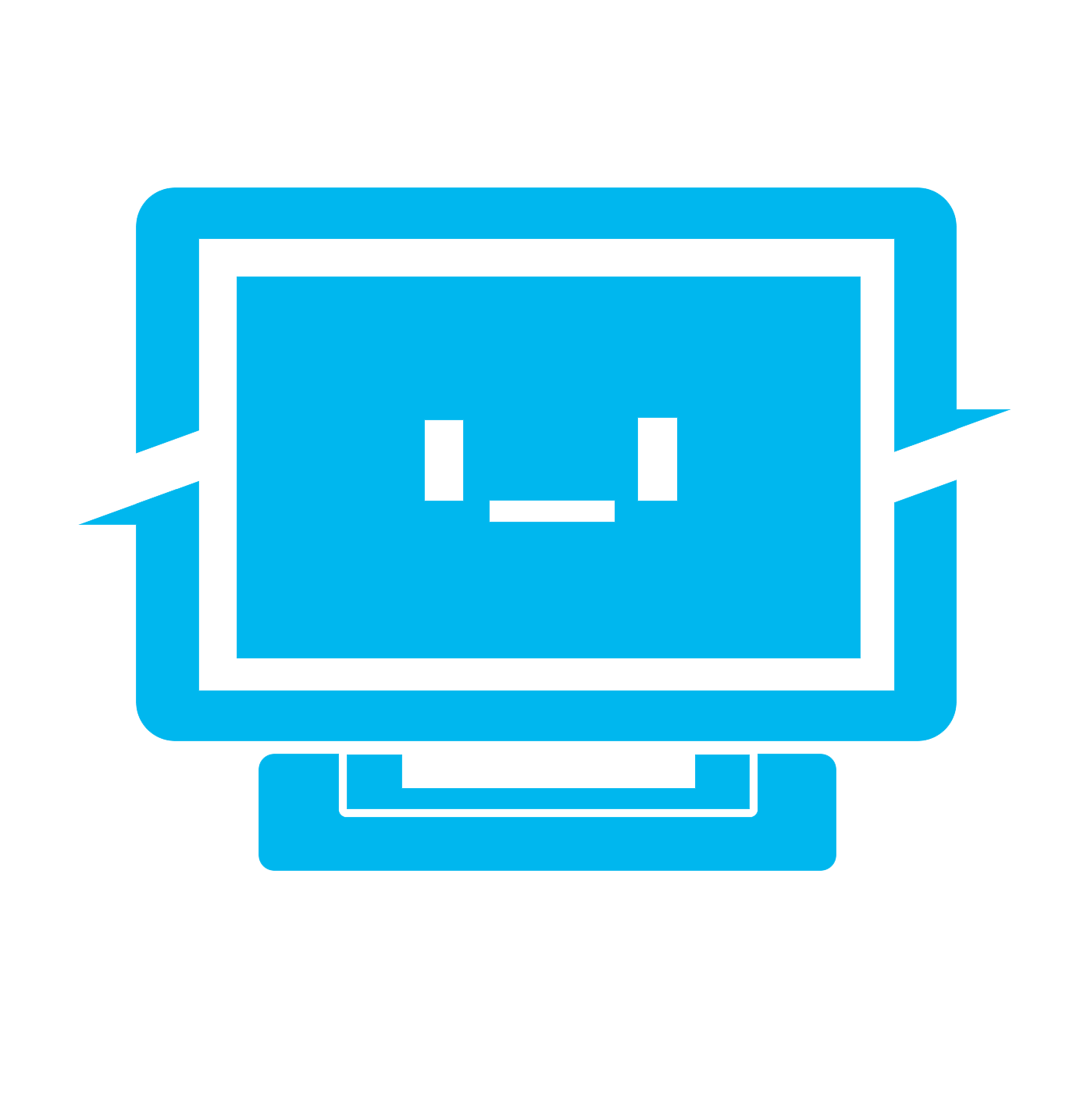这周的周报有点晚。
最近正在经历一场技术祛魅。不知道这个词用在这里合不合适,大概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本来看着高深或者神奇的技术显露出了它枯燥的一面,因此学习热情在各方面进入了“增长率放缓”的平稳期。平日的事情说不上多,但是热情被消磨之后,一些拖延和摆烂的行为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不过既然都写在这里了,我也没有理由再做过多自责。
毕竟上大学以来都是以兴趣驱动的学习(我已经完全抛弃纯粹面向考试或者面向功利的学习心态了),这种驱动力自然有它的一点弊端,那就是新鲜感总有褪去的时候。完全依赖于新鲜感的心态想必是不可能长久的。我倒没有怀疑说自己正在学的东西是否真正有用,但是有时候看不到业界工业实现的一些细节总归是有些让人迷茫。毕竟整天泡在各大媒体宣传的什么“人工智能”什么“元宇宙”什么“云原生”之类的大概念下面,看到的也只有空气大饼。
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大概在周四周五两天吧,主要就是一篇文章和一场srtp立项答辩会的事情。
文章是一篇大佬组织的比赛的复盘https://zhuanlan.zhihu.com/p/470766162
这一篇文章和周五的srtp答辩会倒是真的让我得以看一看现在业内都在整些什么玩意儿(虽然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不是什么真正可以期待短期落地产生效益的项目。而且大家的srtp基本上也都是导师的博士生研究生带着做,套上一些前期成果。说到这里,突然觉得我参加的项目虽然说远不比其他人的听着有技术含量,更像是一个玩具项目,但总归是在本科生的技术视野环境下我能够完全理解的范畴之内,感觉属于是最为务实的一个了)
其实说起来也很奇怪,也就是这样两件事情,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那么一些方向感和动力。所以说心理这个东西真的还是蛮神奇的,所谓学习动力,也不是压力逼出来或者大饼画出来的,而很可能和气压湿度、食堂饭菜以及运动步数相关。
就是这些奇怪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在那些无聊的、只用抄写PPT的各种报告里面水满几千字吧。
(另外,显卡价格一路下跌,本来都到心理预期价位了,现在决定再等等了。lourdraw老师的《夏日幽灵》终于要上架b站了,都已经首映半年了,也就40min的片子,真的等好久了)
封面是河CY画的砂之惑星
本周书摘
本周读完了桑塔格的《激进意志的样式》的最后一篇《河内行记》。另外马原课分到的读书任务是《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第七第八章。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人写的,还是相当有意思的。作者模仿论战的文体,回应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误解和指责。
河内行记
- 在1945年8月之后的一次讲话中,胡志明甚至提出了“让生活积极乐观”的五点诀窍:一、熟悉政治。二、学会绘画。三、懂音乐。四、练习某项运动。五、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因此,说到越南人的乐观主义时,我指的不仅是他们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更是指他们对乐观主义的信奉,将其视作互相理解的一种方式——整个社会都把重心放在不断进取上。
- 高教部长谢光堡教授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丝毫没有嘲弄意味:“美国人教会了我们许多。比如,我们明白了教书育人必不可少的并非漂亮的大楼,就像河内那所理工专业学校的崭新校园,战争升级伊始,我们就不得不从中撤离了。我们躲进丛林、建起分散式学校后,教育水平反而提升了。我们当然想吃得更好、穿得更靓丽,但在这三年里,我们懂得了没有它们,一个人依然可以做许多事情。那些东西固然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需品。”
- 当地人的说法简单多了:这不过是一个你是否拥有足够智慧的问题。美国势不可挡的优势在于人力、武器和资财,而用越南人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已然承受的严重破坏引发了一个切实的“问题”,但他们完全相信可以用他们无边无际又“充满创造力的”工作热情来解决这一问题。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人们在如火如荼地辛勤劳作,因此国家才得以运转。实际情况是,他们将工作均匀地分配在整个国家的土地上——河内大街小巷的人行道边和乡间小道上都放了一些无人看管的大号木条箱;铁路沿线的空地上也摆着一堆堆工具和其他材料,这样一来,轰炸过后几分钟内就能开始抢修轨道。不过,虽然越南人愿意靠着铁锹和榔头一点一点重建祖国,他们是很懂得轻重缓急的。举个例子,空袭过后,通常几天内农民就会赶紧把B-52战机在稻田里炸出的弹坑填满。可我们还看到了一些“2000磅”和“3000磅”炸弹造成的巨大弹坑,大到他们认定难以负担填补所需的时间和劳动,于是把这些大坑改造成了鱼塘。尽管整修炸弹破坏的场所和设施,或是建造新的、有更好保护的地方这类工作从不间断,无休无止,耗去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关于未来越南人还是考虑了很多。想着战后的国家势必需要身怀精细技术的专业人士,越南人并没有发动大学和职业学校的老师教授或者二十万学生中的任何一人来参与这项工程;实际上,1965年之后参加高等教育课程的学生人数在稳步提升。建筑学家已经为战后一定会建造的全新城市(包括河内,北越人完全相信,美国撤退前会把它夷为平地)画下图纸。
- 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的是革命情感的共同体验——不是豪言壮语,不是对社会不公的揭示,甚至不是理性分析,更不是任何权衡利弊后的行动。而在两方面——思想意识与言辞表达之间的不相称,实际意愿的强弱——的共同作用下,革命其实是可以被“谈话”消解殆尽的。(所以法国最近的革命才会失败。法国学生一味空谈——话讲得还很漂亮——而没有在占领的大学里重新组织起行政工作。在外界看来,他们上街示威和对抗警察的场景是言辞和象征层面的,而非实际行为;这也是一种“谈话”。)
在我们这个社会,“理想主义的”往往意味着“缺乏组织的”;“富于战斗性的”的意思仅仅是“情绪激烈的”。在美洲和欧洲,大部分疯狂叫嚣着谴责所处社会的人既根本不清楚自己更想让社会成为什么样子,也没真正考虑过掌权的任何计划,好让激进的变化付诸实际。是的,多半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简直像一种人们特意设计来让它永远成功不了的活动。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项反社会活动,这种形式之所以应运而生,就是为了人们可以通过对抗国家来维护个体的独立性。这是“组织外之人”的仪式性活动,不属于靠着与国家之间热烈的情感纽带团结在一起的人民。 - 毕竟,除了越南人自己,谁会预料到1965年2月7日,这个弱小、贫穷的国家能顶住美军残忍可怕的地毯式火力?可他们顶住了。三年前,开明的世界舆论普遍同情越南,因为知道他们不可能抵挡美国;那时候,反战人士的口号是“越南的和平”。三年后,“越南的胜利”才是唯一的口号。正如河内人告诉我的那样,越南人不需要谁的同情;他们要的是真心的的支持。继续战争,最终落得“悲剧”下场的会是约翰逊和美国政府,黄东说道。“战争结束前,会有许许多多困难,”他补充道,“但我们一直很乐观。”在越南人看来,他们的胜利是“必然的事实”。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单继刚的中文版简评:
作者所设想的读者对象,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研究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或误解的普通读者。
另外,由于伊格尔顿模仿了马克思的论战文体,因此文章显得“凌乱”。
适合人们行使自由的条件,也必然适合滥用自由。实际上,如果没有对这种自由的滥用,任何大规模地行使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许多问题,会发生的大量的矛盾冲突和一些无法挽回的悲剧。
第七章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痴迷论”进行驳斥
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晚期”、“消费主义”、“后工业”或“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基本性质。
第八章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
在伊格尔顿看来,暴力并不是区分改良与革命的标准。有些改良可以非常暴力,比如说美国的民权运动;有些革命可以相对平和,例如俄国的“十月革命”。改良是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但迟早会遇到一个转折点,届时制度将拒绝为改良继续让路。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统治阶级又不愿意交出自己控制的物质资源的时候,改良就会转化为革命。
无产阶级绝不排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但是,议会和国家到头来与其说是代表了广大人民,倒不如说是代表了私有财产的利益,所以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暴力革命的方式恐怕不能避免。
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政治运动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成为后者的思想资源。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学理层面,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文化、性别、语言、他者性、差异、身份认同以及种族渊源等议题,均与国家权力、物质不平等、劳工剥削、帝国主义掠夺、群众政治反抗行为和革命改造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书中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本书缺乏哲学史的视角
第二、本书否认唯物史观是“决定论”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对阶级的无聊痴迷。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自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以来,社会阶级的图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会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越来越不重要的社会世界里,流动性越来越大,在这里谈论阶级斗争就如同谈论在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那样不合时宜。革命工人和戴着大礼帽的邪恶资本家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凭空想象。
原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并非是以风格、地位、收入、口音、职业或墙上挂的是鸭子还是德加的画作来定义的。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男人和女人一直在战斗,有时甚至付出了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终结势利行为。
原文:美国有一种相当离奇的“阶级主义”概念,它似乎想说明阶级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中产阶级应该停止蔑视工人阶级,就像白人应该停止自以为比非洲裔美国人更优越一样。但是,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一个态度问题。阶级之于马克思,就如同德性之于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你感觉如何”的问题,而是“你在做什么”的问题。
原文:混淆差异、瓦解等级,把最多样化的生活形式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正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没有哪种生活形式比资本主义更加混杂和多元化。当涉及到底谁应该被剥削时,这一制度显示出令人钦佩的平均主义。只要是有利可图,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老人、维克菲尔德的街区和苏门答腊的乡村,都是它压榨的对象,都会受到无可挑剔的公正对待。但是,造就这一平等现象的原因是商品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
原文: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钦佩资产阶级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坚决反对政治专制、财富的大量积聚带来的普遍繁荣的前景、尊重个体、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真正的国际社会共同体,等等,正是这些成就必将成为社会主义自身建设的必要基础。……然而,资本主义赋予这个世界的强大礼物之一恰恰是工人阶级——这是一股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培养起来,却最终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秩序诞下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一景象颇具黑色幽默的色彩。
原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目光聚集到工人阶级身上,并不是因为它看到劳动者身上具有某种灿烂的美德。盗贼和银行家也在辛苦打拼,而马克思并不是因为赞赏这些人而闻名于世的。……工人阶级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只有那些身处这个制度内部,熟悉其运转方式,被这个制度组织起来成为一股既有技术又有政治意识的集体力量的人,才是这个制度成功运转不可或缺、却会从推翻这个制度中获得物质利益的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最终接管这个制度并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运营它。
原文:马克思本人似乎把社会阶级视为异化的一种形式。把世间的男人和女人简单地称为“工人”或“资本家”,实际上是用一种平庸刻板的分类掩盖了他们独特的个性。但,这是一种只能从内部才能消除的异化。只有通过全面认识阶级,承认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虔诚地希望其自动消亡,才有可能将其摧毁。……人们被匿名归类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异化,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讲则是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
服务业、信息和通讯业巨大发展并没有使工人阶级消亡,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反而是巩固了这种财产关系。为人熟知的无产阶级将大量消失,同时大量的工人阶级转变为中产阶级,或者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中产阶级发现,他们正重新陷入曾经让19世纪的无产者苦不堪言的经济不安全状况。”
马克思所刻画的那一个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具体的人,倒不如说是一种制度下的化身。社会的最高层并非一个邪恶的资本家阴谋集团,而是由一些具体的人组成的。他们或许本身并非资本家,但是却直接或者间接充当着资本的代理人。这与他们的收入方式(资本、租金还是薪水)无关。
所以很大程度上阶级对立的矛盾并非人心的善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就的。
原文:我们应该指出,只有那些认为阶级就是工厂主穿长礼服而工人穿连裤工作服的人,才会接受工人阶级已经消亡这种非常愚蠢的观点。他们深信阶级已如冷战一般寿终正寝,并因此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文化、身份认同、种族渊源和性别等问题上。然而,在当今世界,这些事物依然像过去那样同社会阶级紧密交织在一起。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行为。他们拒绝温和渐进式的变革进程,而选择血腥和混乱的革命。一小撮暴动者将揭竿而起,推翻政权并将他们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大多数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制度势不两立的原因之一。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道德蔑视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因此根本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而感到不安。为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多少生命可能会在这一进程中逝去也在所不惜。
原文:马克思主义并不以暴力程度为标准来定义革命,也不认为革命必须是剧烈的动荡。俄国并没有在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后的一夜之间就废除了市场经济和实现了全部工业的国有化。与此相反,市场和私有制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很长时间内仍然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布尔什维克人是以渐进主义精神来逐步将它们取消的。党内左派也是以相似的态度对待农民阶级的。依靠武力把他们赶进集体农庄当然不成问题,但与此相反,整个过程却采取了循序渐进和协商解决的方式。
夺取政权在一朝一夕之间,但是对社会传统、社会制度、情感和习惯、旧有的文化等因素的改造势必是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的变化需要通过长期的教育和文化熏陶才能实现。”
绝对的和平主义是极不道德的,在极端情况下,暴力的使用是有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会走弯路,会诞生如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这样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在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的紧急制动,而不是革命本身是失控。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不满的发泄,而是有着明确的组织性、政治诉求的变革。不能够狭隘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是颠覆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新旧政权的更替。
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依赖革命,或者说不完全依赖。只有极左翼的分子才会对革命抱有狂热幻想。但是,议会有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来自于议会的一组矛盾:普通民众被劝导将自己的权力永久委托给议会,但是他们对议会却几乎毫无控制能力。议会制民主,恰恰来自于这种“代言人政治”的不民主。
革命不是一些人策动和叛乱就能够发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了解到革命的代价(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还有整个社会的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只有当现状恶化到再维持下去的代价超过了革命的代价,革命才会真正爆发。
资本主义在某些意义上可以说是它自身蕴含的矛盾让它土崩瓦解。而社会主义的政权则在资本主义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让尽可能少的人受到伤害。
(彩蛋:
女权运动诞生之初,一些出于善意却弄巧成拙的男性作家曾经写道:“当我提到‘人’这个词的时候,我指的是‘男人和女人’。”在此,我也想以同样的方式声明,当我提到马克思的时候,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就与本书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