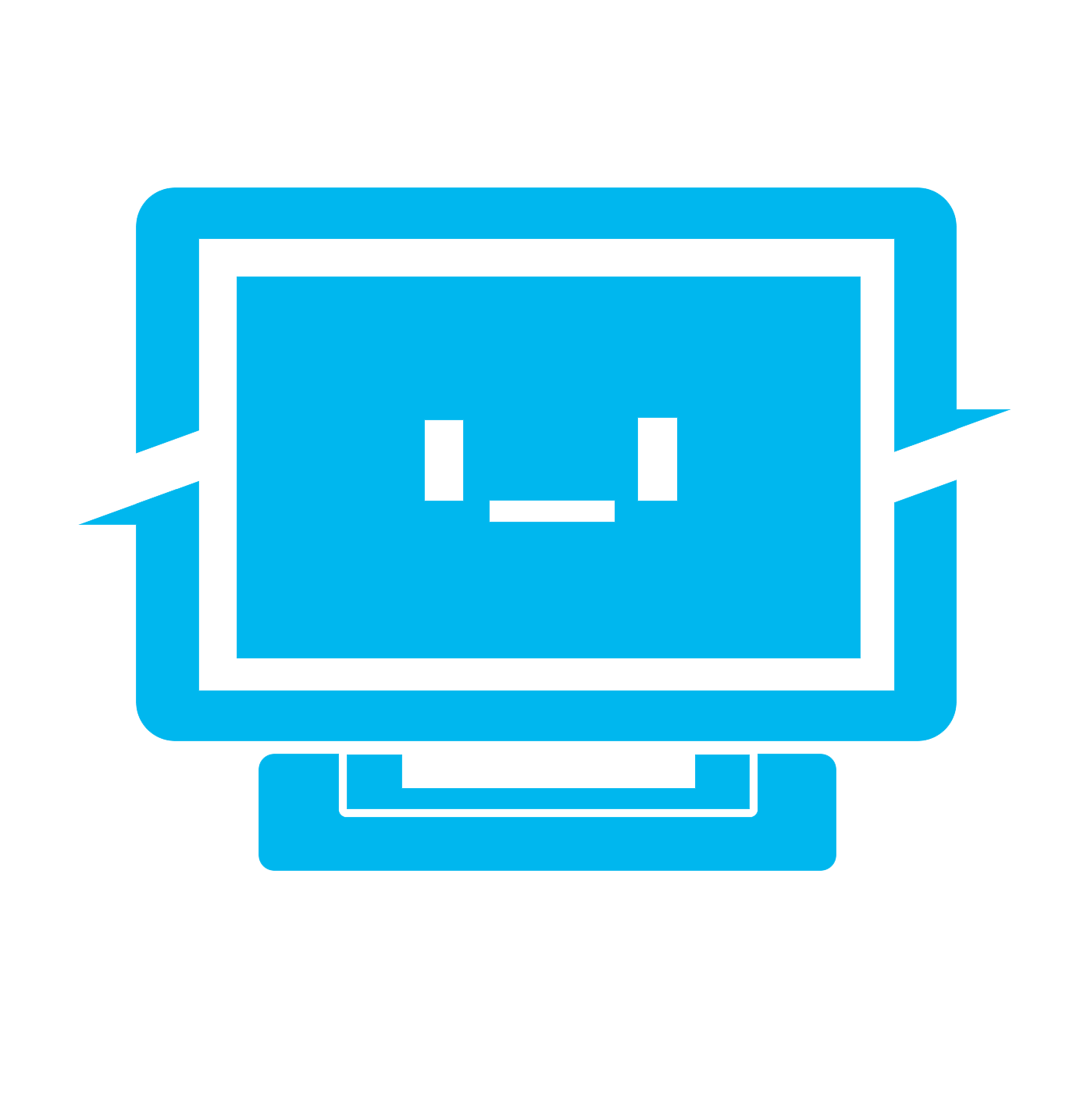疫情意想不到地在这个时候反扑。最近七天很多高校都封校了,而我身边的好些同学也被送去了隔离(虽然浙大没有完全封闭,但是已有一大批人被转移到专门的宿舍和酒店去观察了)。虽然不是自己去隔离,虽然不是自己隔离的时候想到的,大概也是一时间看到同龄的学生们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纷纷吐槽,周二的时候看到顶置热搜大大的“青春有几年,疫情占三年”。不知怎么的,突然觉得高中的关于“自由”的作文母题是否缺少了一些方面的讨论。
我时常觉得那些话题其实的可说的有很多,但出成题目,好像少了某些方面的探讨,但面向题目思考立意的时候总感到一种奇怪的束缚,一种对探讨方向不自觉地划定。就比如说“自由”这个题,总是让你去和“放纵”联系,是和约束和枷锁去联系。其结果就是,我在抓着一些脱离生活的事件展开在文章中的探讨。总结下来不过就是自由固然可贵,但要远离放纵,“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自由”。曾想起高中同班有一位总爱在作文里表现其浪漫主义风格的同学,遇见这种题大概率是要通篇抒发“自由”在感官上的如何良好,人生活在自由中的状态从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是多么地完美和完全。不过这样的考场作文不是打高分就是要偏题跑题的。不过分数的忽上忽下并不妨碍这位仁兄的作文被同学们热捧。在大家都挠破头去取悦素未谋面的阅卷者时,借考场作文的体裁写点真性情的东西倒真是一种伟大的反抗。
自由这个词往往被放在一个比较抽象和宏大的地方被探讨(比如革命者口中的自由),但是我们平常所能直接接触到的,好像大多是感性层面上的,所谓自由的感觉。即使具体到这种对自由的觉感上,又有太多种类型可以分出来。比如说,想要去旅行,走遍全球,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自由?想要逃脱日常的时序和规律,从生活中出走,这是怎样的一种自由?这些自由和“从心所欲不逾矩”,“列子御风而行”的自由是一样的自由吗?他们有高下之分吗?给他们直接定性为地理格局上自由,时间尺度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等等,应该会流于狭隘。
这些问题都可以挖进去很深很深,因为这关于人精神上和谐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放纵”和“约束”上的道德说教。学生们总喜欢引“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刻处于枷锁之中”。每每引到这句话,大多数人都会凭空回忆起那些求而不得的经历,而这句话仿佛就给日常中的那些问题指了一条简单的路——“打破枷锁”。问题是,对于某些“枷锁”,我们真的关心吗?地心引力每时每刻都在抓住我们的双脚,除了要上天,我们平时也没有抱怨过它什么。我觉得考场作文里用这句话,更像是在预设一种情感色彩,在挑起一种对立。
一方面我在想,自由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是价值上的一种“关怀”,另一方面我又在想,它是否因其自我显现的需要而变成要考虑参照物的一种否定式宣告。而这种对约束的否定宣告是否可能成为一种自由的滑落?滑落为一种带有政治正确性质的,道德规训?或是一种抽象的包装过的商品与消费行为呢?这些是我在高中隐隐感觉到空缺存在但直到现在才能明确说出来的问题,是在讨论“约束”和“放纵”这些问题之前的问题,而且或许约束和放纵这些事情在这两个问题面前并不重要。
话题太大,或许我在这里也只能是抛出问题,留给以后的我去慢慢感悟了。
有很多人批评《后浪》没有看到普通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但是看到《入海》,给予了肯定又如何?我觉得不过是拿着“奋斗”或者“打拼”再讲一个故事罢了。所谓“人生无边界”这种事情,就一定要走到生活的最边缘才能被宣告吗?我们日常所行所为,本就是人生的n次方中的其中一种,那为什么只有“叛逆”和“出走”才会被认为是自由?又或者“奋斗”才是青春本色?我为什么在丢下一本剧本的时候,又要拿起另一本剧本呢?
“青春有几年,疫情占三年”。发出这样的感慨的时候,我们又是否给自 己设限?我们是否真正地得到了自由或者青春,还是说我曾经做过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我感受过“自由”和“青春”。还是说这种自由和青春是被“赋魅”的,如同爱情一般,在“祛魅”后就一无是处了?
不过,话说回来,倒不如说这条热搜tag是一次学生的集体情感宣泄,或许本来也就没什么事情,大家吐槽吐槽罢了。
前几天我还说,疫情占掉的三年不要算岁数好了,大家都还刚刚成年,十七八岁,十年青春,一秒都没过去。
对于旅行,刚好菜头叔这星期写了一篇,摘一些下来放这里:
越是隔离,我就越怀念旅行。但我其实并不算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我嫌麻烦。不像我的许多朋友,一年两次外出,精准如服药,到点就必须去。以前觉得收拾行装,购票乘机很麻烦,现在有了猫就更觉得麻烦。……
如果不去考虑所有的麻烦,旅行是对日常生活的反对。首先是剥离了工作,然后是剥离的熟悉,最后你的确知道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游荡,先前所有的一切都距离自己极为遥远,那就是自由的感觉。
平日里一个人总是会忍不住去想等我有了钱就能,等我换了工作就能,等我买了大房子就能,等我换了新汽车就能……这是以拥有作为基础的自由,以为自己一旦拥有了某些东西,心灵就会更少束缚,获得更多自由。旅行就像是一把刀子,直接切断这些妄想,不单没有得到这些东西,反而要让你失去周围拥有和熟知的一切,这时候人反而会觉得轻快起来,倒不是因为风景和风情。
我看见许多人虽然在记录自己的旅途,但无非是从一处咖啡厅换到另一处咖啡厅,从一处自助餐换到另一处自助餐,他们还是那样坐在桌前,连姿势都没有变过。网红才是最好的教师,无需布置作业,更不必用跑圈和教鞭威胁,人们自觉主动地学习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姿势,甚至是他们用过的角度,然后对着手机摄像头复刻一遍。有无形的手在操纵一切,对于许多人而言旅行同样意味着格式和规范,其中并没有漫无目的的游荡,只有完形填空。
我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去到一个新地方就已经足够值得欢喜。其中有些人却是在找寻,在生活之外找一个处所,在那里找寻自己的理想生活。……他们并非是在旅行,而是在回归,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某种静谧的田园生活,或者更适合生活在温暖湿润的海边。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投胎时的空降错误。落到了错误的地点,需要用旅行来修正。
每个人对于旅行的期待并不相同,理解也大相径庭。但是大家的处境却是类似的,那就是许久都不曾外出旅行,想着要去什么地方走一走。在经历了那么多不许可之后,需要找个什么地方感受一下什么都许可是什么一种感觉。甚至连感觉都不需要,找个什么地方发下呆也是好的,因为什么都不去想也是一种奢侈,如同突然赦免了某种必须的义务。
本周书摘
主要还是苏珊·桑塔格的《激进意志的样式》。《戏剧与电影》这一篇后面跟了很多对具体电影的评价和剖析,但是由于我没有看过这些电影作品,实在是没法和作者同频共振,遂跳过。最后两篇是《美国怎么啦(1966)》和《河内行记》,偏向政治评论文。之所以说是偏向,是因为《美国怎么啦(1966)》不是真正的对政策做评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正确”评论;同样的,《河内行记》虽然是越战时期的反战游记,但切入点仍然是美国和越南两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而非将镜头对准战争本身。苏珊很清楚地在她的作品里面给自己划定了界限,而且她在踏出对于文化的批评这个圈子之外时非常的小心谨慎,她时刻反思自己所处的立场和原生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像某些“公知”一样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全世界通用一样。
《河内行记》篇幅很长(是由很多篇日记组成的),还没看完。下次再贴书摘吧。我在里面看到一个说法觉得很值得思考。苏珊说共产主义下的越南人的生活是集体主义的,他们的意义体系是“历史的”。这一点和美国是不同的,美国的意义体系更倾向于“心理的”(苏珊说越南人比较缺乏美国这种“心理的”生活)。她认为在这种“历史的”意义体系下,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二维的(或者说扁平的)。她认为在越南,大多数事情被放置在一个历史性的角度去考虑,而生活在一个很会造神和讲故事的体系下的人是幼稚的。而在美国的“心理的”社会中,她认为更加立体,是“成人的”。
我看到这里,便理解了为什么同样是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同样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法国爆发的是“红色五月风暴”。苏珊直接点明,欧美左派知识分子群体认为共产主义,在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这一向度上必须进行解放,而越南的意义体系并不让他们满意(文化并没有被解放出来)。
“自省”:反思齐奥兰
- 意义淹没在生成的潮流中:即毫无目的、连篇累牍的出现和废弃的循环运动。人的生成就是耗尽其可能性的历程。
-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西方最好的智性和创造性思考在整个人类生活期中似乎无可辩驳是最具活力、最深入、最敏锐、最有趣和最真实的。然而,同样无可辩驳的是,所有这些天才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意识到自己立于思想的废墟中,濒于历史和人类自身毁灭的边缘。(我思故我在因而盛行。)最明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日益成为这些生成中的废墟的早熟的考古学家,或义愤或坚忍的挫折诊断专家,或高深莫测的编导,在恒久的天启时代,主导着个体生存必需的复杂精神活动。追寻新的共同愿景的时代可能也已结束:如今,无论是最乐观的和最沮丧的,最愚蠢的和最睿智的,都已有定论。但个体对精神引导的需求却前所未有地迫切。各自逃生。
- 哲学成为痛苦的思考。思考吞噬着自己,尽管(也许正因为)在重复地自我残杀,它却毫发无伤地继续发展着,甚至还兴盛起来。在思想的激情表演中,思想家既是正面角色,又是反面角色。他既是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又是那只冷酷的鹰,啮噬着普罗米修斯不断新生的内脏。
- 阅读凯奇,让我们意识到,齐奥兰仍然局限在历史化意识的前提中。虽然他渴望超越那些历史化意识的姿态,还是无可避免地继续重复它们。因此,齐奥兰的思想必然是处于对这些姿态痛苦的重复和恶真正的重估之间。也许,只有像凯奇那样的思想家,才能做到完全重估,因为他们承继的这个文明中的苦痛和复杂,大部分已经被他们抛弃——这究竟是来自精神力量还是精神冷漠则是次要问题。齐奥兰热烈而又极富争议的推测,出色地总结了西方思想迫在眉睫的衰败,但除了理解之后的满足感之外,并没有提供任何解脱之道。当然,解脱根本不是齐奥兰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分析诊断。要想解脱,可能我们必须放弃拥有知识和由此感受所带来的优越感——这种局限性的优越感业已让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 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完全是一种思想病,总是希望四处为家。”如果人的思想可以四处为家,那他最终必然要放弃这局部性的“欧洲”优越感,让其他的东西——也许看来冷漠奇怪,智性上也很简单——进来。凯奇用他独特绝妙的反讽写道,“只需要给它时间中的一段空寂,让它充分展示自己的迷人之处。”
戏剧与电影
- 但为什么戏剧被说是电影的淘汰品呢》那些提出淘汰机制的预言都建立于这样的一种逻辑: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存在的特定目的,从而当另一种事物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时,淘汰就发生了。然而,戏剧的存在是否就是凭其禀赋实现某个目的,而电影又正好能更好地实现该目的?
那些预言戏剧将消亡的人声称电影涵盖了戏剧的全部功能,并试图辩称,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就如同照片与绘画的关系。如果绘画的全部作用就是复制原型,那么照相机的发明确实就可以淘汰绘画了。但是美术作品不仅仅是图片,电影也不是被民主化的传达给大众的戏剧(因为电影是标准化的便携物件,便于复制和传播)。
在照片与绘画的不复杂的关系里,后者只需宣称一点即可暂时摆脱被淘汰的困境:绘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抽象。照片的现实性明显占有优势,但同时也解放了绘画,使其得以发展抽象性。同理,电影展现(而不仅仅是激发)想象的强大力量也被认为是鼓动了戏剧,使其放弃了传统的“情节”模式。
美国怎么啦(1966)
- 外国人歌颂美国的“活力”,将我们无可比拟的经济繁荣与艺术娱乐中的勃勃生气都归因于它。但这活力的源头无疑是有毒的,我们为之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苦果就是一种非自然的、反人性的、失衡的动力,把所有人的神经都折磨得苦不堪言。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暴力的活力,一种不受约束的怨恨与焦虑——此二者都是由长期的文化紊乱所释放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活力必须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得到升华。而它升华后的产物大体上就是粗俗的物质主义与贪婪。就是狂热的慈善。就是愚昧的道德运动,其最令人瞠目的代表便是禁酒令。就是一种让乡村与城市面目丑陋的可怕天赋。就是少数牛虻的多嘴与叮咬——艺术家、先知、丑闻记者、怪人与疯子。就是自我惩罚的神经症.但赤裸裸的暴力依然不断地冲破表象,让人们对这一切疑窦丛生。、
- 就在险些成为世界末日的那一天——美国与俄国当时正在古巴海岸边剑拔弩张——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道:“我——我不担心。我已经在上一场大战时服过役了,如今也过了服兵役的年龄。他们没法再拉我去了。可我举双手赞成现在就给他们一点厉害尝尝。我们还等什么呢?早打早完事儿。”既然战争永远发生在“那里”,我们又总是赢家,那干嘛不扔炸弹呢?要是按一下按钮就完事儿了,那就更好了。美国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既是一个能毁灭世界的国家,又是一个生怕有损一根毫毛的国家。一位普通的美国公民也许心怀约翰·韦恩的狂想,但他的脾性却时常跟简·奥斯汀笔下的伍德豪斯先生一模一样。
- 我不认为美国白人致力于给予黑人以平等。致力于此的只是一小部分美国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受过教育,家境优渥,但几乎没有与黑人有过长时间的社会接触。这是一个狂热种族主义的国度;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依然如此。
- 一种刻意模糊性别差异的新时尚似乎在如今的年轻人当中流行开来了,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青春雄激素诞生了。……而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里见证“西方男性的极端异变”,一场“反对阳刚之气的叛变”,甚至是“对于传统男性力量的摒弃”。对于费德勒而言。这种个人道德观念的转向是可悲的。……老派的激进政治(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某个版本)意味着依然认可传统的“清教徒式”价值观——工作、戒酒、成就、建立家庭。……年轻人中间的这样一种新风尚一定在本质上是对政治冷感的,而他们的革命精神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病。至于同样是这群年轻人为何也加入了非暴力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或是登上了“北极星”核导弹潜艇搞抗议,或是支持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同时又抽大麻、双性恋、崇拜“至上”乐队,费德勒等人的看法是将其视为一种矛盾,一种道德欺诈,或是一种智识上的意志薄弱。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性别的去极化——就拿让费德勒如此着魔的这一点来说——代表着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许也就是它的消解),这一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性革命已经超越了前一个阶段,也就是将性视作人类活动的一个受到戕害但分离独立的区域,或是发现是“社会”压抑了对于“性”的自由表达;性革命当前的发展程度已经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个性表达的常用选项几乎完全压制了对于愉悦的深层体验,抹杀了自我认知的可能性。……年轻人的眼光已经超越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没有什么不对。让教授们去守护那份确实珍贵的遗产,履行虔敬者的一切职责吧。如果说年轻人不再向那几尊异议者的旧神行礼致敬了,那也没有什么好哀声叹气的了。
……
他们当中当然混进了许多冒牌货、笨蛋和真正的疯子。但他们中的精英确实怀着一种复杂的渴望:既参与,又“逃避”;既要做善良的人,又要做视觉上和触感上美丽的人;既要充满爱心、温文尔雅,又要斗志昂扬、富有效率——这些渴望在我们当前的形势下都是有意义的。